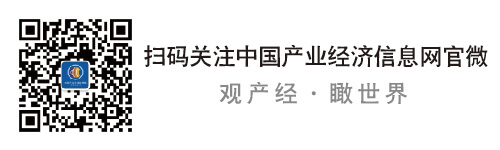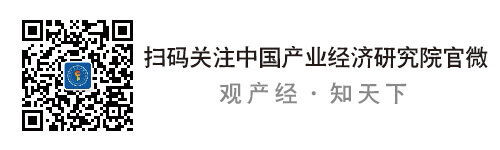1519年5月2日,在巴黎东南约220公里的卢尔河畔昂布斯堡镇,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在克劳斯-卢契小庄园中去世,迄今整整500年。瓦萨里在《艺术家的生活》里描绘,达·芬奇临终前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怀抱着,他沉痛忏悔“没有奉献应该达到的艺术成就”。这或许指的就是他在生命尽头也未能最终完成的旷世杰作《蒙娜丽莎》。
芬奇山镇走出的列奥纳多
达·芬奇的全名是Leonardo di ser Pieroda Vinci。da Vinci是指他的出生地佛罗伦萨西北约50公里的芬奇小镇。di ser Piero是指他是绅士皮尔诺的儿子。Leonardo(列奥纳多)才是他的名字。皮尔诺20岁左右从贫瘠的芬奇山区进入佛罗伦萨独立创业,很快就成为一位活跃于上层社会、非常富有的公证人。1451年夏天,25岁的皮尔诺回到家乡芬奇镇,与一位山村姑娘相好;1452年4月15日,这位姑娘为皮尔诺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即达·芬奇,然而,皮尔诺并没有与这位姑娘结婚。
达·芬奇生母的身份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学术课题。按照著名的达·芬奇研究专家、牛津大学教授M。克姆普与意大利经济学学者G。帕兰帝合作的《蒙娜丽莎:人与绘画》一书中的考证,达·芬奇母亲名叫卡苔莉娜(Caterina di lippo)。卡苔莉娜生于1436年,在1451年与达·芬奇父亲相遇时,是一位父母双亡、并带着一个年仅两岁的弟弟的贫寒人家女孩。卡苔莉娜生下达·芬奇一年后嫁入一个普通的山村人家,而且生育了5个孩子。在达·芬奇67岁的人生历程中,卡苔莉娜只在他上万页的笔记中出现过两次。一次写道:“1493年7月16日这天,卡苔莉娜来。”另一次写道:“一个来自佛罗伦萨的卡苔莉娜在米兰莫蒂书馆死亡,1494年6月26日。”同时,在米兰官方的死亡登记册中,还有一个由达·芬奇支付的卡苔莉娜葬礼的费用清单。达·芬奇笔记本没有出现“母亲”一词。克姆普与帕兰帝认为,虽然达·芬奇没有称卡苔莉娜为母亲,但根据多种文献对证,他的两条笔记证实卡苔莉娜就是他的母亲。
达·芬奇的父亲皮尔诺一生经历了4次婚姻,前3位妻子均早逝,只有第4位妻子在他之后去世。皮尔诺的4位妻子给他生了16个孩子,加上达·芬奇,他一共生有17个孩子,其中数位夭折。达·芬奇出生后,先由母亲哺育。因为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祖父1457年的纳税单上,一般推测母亲养育他至5岁。但是,卡苔莉娜生下达·芬奇的次年就出嫁了,而且很快生育,因此达·芬奇也可能1岁左右就到了祖父家。根据非常少的文献记载,达·芬奇在祖父母和一个叔叔的抚养下,在芬奇小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472年(或1466年)至1482年,和1500年至1504年,达·芬奇与父亲两度共同生活在佛罗伦萨。但是,无论父亲还是父亲的孩子众多的家庭,都没有在他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什么痕迹和影响。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十数位异母弟弟争夺叔叔遗嘱留给达·芬奇的遗产的诉讼,直到达·芬奇死时都没有终结。皮尔诺1504年78岁时死亡。达·芬奇记述道:“1504年7月9日星期三,7时,公证员皮尔诺·达·芬奇在波德斯达宫逝世,我的父亲,在7时。他80岁。他留下十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这样独特的家庭背景,使非婚生的达·芬奇成为一个多余的孩子,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不是这个孩子的心灵呵护和精神依靠。他对于自己的孩提生活,只有两则记述。其一,他记得自己年幼时重复做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摇篮中,被一只飞扑下来的兀鹫反复将其尾巴插入口中。其二,他带着好奇和恐惧,进入一个他自己发现的神秘洞穴中探险,试图探明里面存在的东西。关于这两则故事,具体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表明童年生活给予达·芬奇心灵深刻的孤寂,甚至是一种梦魇般恐惧的情感空白。这或者可以让我们解释达·芬奇为何采用毫无感情色彩的“簿记”记述父母的死亡。因为父亲和母亲在他的现实和精神生活中,都是一个无可叙述的空白。
弗洛伊德认为,童年被迫离开母亲的达·芬奇具有强烈的恋母情结——“兀鹫尾巴插入口中”是达·芬奇想象自己吮吸母亲乳头的潜意识表现。他更进一步认为,正是出于恋母情结的无意识冲动,使达·芬奇的肖像画成为他想象和塑造母亲形象的艺术形式;因为“母亲”是一个模糊的原型,也导致了达·芬奇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如饥似渴的持续探索。弗洛伊德的论述过于倚重于儿童对母亲的心理需要,忽视了父亲在孩子心理成长中同样不可或缺的位置。如果说母亲卡苔莉娜的基本缺席,在达·芬奇的成长历程中留下的是空白;那么,年龄最长、却是唯一的非婚生子的达·芬奇,在事业兴盛的公证员皮尔诺的家庭中,见证的是继母更替、异母弟妹成群,从这位父亲那里将更强烈地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外”和“多余”。因此,从心理补偿原理讲,父母之爱的双重缺失,为达·芬奇的心理成长留下了无可填补的空白;而对这个空白寻求填补的动机,成为达·芬奇毕生永无衰减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力量源泉。在芬奇小镇寂寞的背景下,孤独的小男孩达·芬奇那个钻入一个黑暗洞穴的身影,把对父母之爱的饥渴和对世界秘密的好奇,浓缩成一颗无限探索和创造的心。未来的历史会证明,这颗心沉默无声地将自己熔铸、锻炼成人类心灵史上最纯粹和坚韧的灵魂结晶。
文艺复兴的伟大灵魂
在人类文明史上,达·芬奇是屈指可数真正代表自己时代高度、并且长久照耀未来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还会产生另一个与列奥纳多一样知识广博的人,他不仅在雕塑、绘画和建筑诸方面知识过人,而且还是一位极其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不知道达·芬奇的教育历程,但从他留下的13000余页手稿,可以推测他成年前接受过非常良好的人文学、数学等基础学科的教育。他以画家闻名后世,但一生中,他被聘用为建筑学家、机械工程师、地图测绘学家和运河设计师。他几乎研究了当时所有的科学门类,尤其是对生理学、解剖学和植物学投入了毕生精力——他解剖了30余具尸体,并著有解剖学著作。达·芬奇的博学和深刻,歌德赞叹说:“今天我阅读达·芬奇《论绘画》,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对它所讲的内容一无所知。”
爱因斯坦说,如果达·芬奇发表他的科学研究,人类科学发展要提前半个世纪。作为文艺复兴的伟大灵魂,达·芬奇提出与经院哲学相背离的新知识论。针对经院哲学以信仰为核心建构知识体系,达·芬奇主张理性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他说:“智慧是经验的女儿”“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以知觉为源泉的”。但是,他并不排斥理性,他说:“必然是自然的女主人和导师。”相信必然,就是相信理性的神圣和完美,相信在这个可见的世界隐藏着永恒的秩序。这就是达·芬奇的自然,或宇宙。
正因为推崇经验的意义,达·芬奇把“眼睛”的认识意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把绘画也提升到“科学之科学”的高度。他说:“眼睛被称为心灵的窗户,它是智力借以欣赏自然的无限创造的第一工具。”这样推崇眼睛的认识意义,与柏拉图为西方认识论提出的理性主义路线是截然相反的。柏拉图认为,眼睛只能观看影像,是最容易受假象、幻象欺骗的感官。他认为认识真理,只能靠理智——灵魂的舵手。柏拉图认为,绘画作为眼睛的艺术,就是停滞于表面现象(幻象)的艺术,因此,他反对绘画。达·芬奇则认为,自然世界和人类个体,从表面到内部,不仅是互相联系的,而且遵循着统一的和谐秩序。这个秩序,就是可以总结为数学比例的必然。因此,一个画家要画出的形象,不仅是外在直观的真实,而且是内在秩序的真实——要由外在的美呈现内在的必然。他说:“只有数学家才有资格解读我作品中的要素。”在这里,达·芬奇揭示了他所追求并体现的文艺复兴艺术(不只是绘画)的理想:以完美的理想表现自然,即创造高于自然的世界真实——第二自然。正是在通过描绘直观个体形象而展现世界普遍真理的意义上,达·芬奇主张真正的绘画必须是“世界之画”。他说:“一个画家是完全不值得赞扬的,除非他是世界的。”
迄今为止,达·芬奇是全球最享盛名的画家。他享年67岁。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真正可以归属于他亲手创作的油画和草图,仅30来件,其中还包括数件未完成作品。在文艺复兴三杰中,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年寿最长,89岁;拉斐尔(1483-1520)年寿最短,37岁;达·芬奇年寿居中。米氏和拉氏的作品数量都远超达·芬奇。但是,当我们试图理解和评价达·芬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卓越非凡的艺术家对于人类文化的意义,不在于他们做了多少,而在于他们做了什么。
1498年,达·芬奇在米兰完成了伟大壁画《最后的晚餐》。这位46岁的佛罗伦萨画家,至少在意大利北部,赢得了盛誉——历史的延续发展证明,在这个中世纪的常规圣画主题发展史上,达·芬奇的伟大创作赋予它最具挑战的人性意蕴和宗教象征。但是,达·芬奇之作为达·芬奇的天才和伟大,必须在人类文化史进入16世纪的黎明时分才真正展现。
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
1499年,因为米兰大公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被黜,为其服务了17年的达·芬奇离开米兰,辗转一年多,回到佛罗伦萨。1500年,重返佛城的达·芬奇已年届48岁,大概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怀。在做了两年地图测绘学家和运河设计师后,1503年,达·芬奇获得了两个订单:一个是佛罗伦萨新市政厅的壁画之一《安吉里之战》,一个是《蒙娜丽莎》。无疑,两相比较,如果要在佛罗伦萨赢得盛名和威信,倾力完成市政当局的订单《安吉里之战》是不二之选;《蒙娜丽莎》不过是当时显赫一时的富商乔康达妻子丽萨的肖像画,无论如何成功,它都不可与前者同日而语。更何况,作为达·芬奇的艺术竞争对手,刚完成巨型雕塑《大卫》的米开朗基罗也获得在对面墙上作壁画《卡欣那之战》的订单。然而,达·芬奇只做了一个《安吉里之战》简略的草图,就放弃了这个可以为他赢得盛名的订单。相反,对于私人订单《蒙娜丽莎》,从1503年到1506年,达·芬奇创作了4年,仍然告知他人没有完成此画。1513年至1516年,达·芬奇进入教皇里欧十世的宫廷服务,后者鼓励他完成这个作品。1516年,弗朗索瓦一世以聘用机械设计师的名誉延请达·芬奇到法国安度晚年,达·芬奇将此画随身带到法国。据文献记载,直到1517年,达·芬奇仍在他客居的克洛·吕斯城堡中修改《蒙娜丽莎》;1519年他逝世时,这幅“未完成”的画作仍然在他身边。
现在,这幅跨越了500年岁月的伟大肖像画被安置在卢浮宫德隆馆的意大利画廊作常规展示。这幅木板油画的尺寸是77 厘米×53厘米。在卢浮宫十数万件收藏品中,只有这幅中小尺寸的藏品被安置在镶嵌防弹玻璃的壁龛中展出。在比肩继蹱的人流中,当你被拥挤着裹挟到可以清晰观望画面的壁龛近前时,端坐在画面前景、左手放在扶手上、右手放在左手上的丽莎显现在你的眼中。她上半身近于笔直地端坐着,身后的背景是隔着阳台护栏、由近及远的山水风景。丽莎的坐姿构成了一个清晰、稳定的金字塔造型,并且占据了画面的主要空间。与在透视中退缩向背景深处而渐入暗淡虚渺的山水相反,丽莎在画面的身姿呈现出一种纪念碑式的挺拔感——这是人类绘画史上,首次在自然大背景上展示一个人真实独立的存在。
丽莎以四分之三的侧面姿态从右向左凝视着我们。她的左肩比右肩高一些,身后背景中的地平线也呈现相应的高低差异。因此在静止的画面上,她的略显俯视的眼神传达着目光流动的意味,而且她的头部和胸部似乎也在作相应的轻微转动。丽莎的姿态和形象,是欧洲肖像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在15世纪后期,意大利流行的肖像画是严格侧面的,像主眼睛也是侧面的,面无表情地看向面对的画框。丽莎不仅以四分之三的侧面凝视着观众,而且以意味幽妙的微笑与观众交流。在达·芬奇描绘丽莎之前,意大利女性的微笑只存在于诗歌中。但丁在诗中如此描绘初恋情人贝德丽采的笑容:“她展露微笑的瞬间,她的容颜超越了言词,心智不能容纳它,无比丰富的奇妙不可捕捉。”(《新生活》)通过《蒙娜丽莎》,达芬奇的画笔把女性微笑无限微妙的意蕴和魅力呈现在画板上。无疑,在画中丽莎全部的真实和生动中,她那双秀美的眼睛在对观众的凝视中漫溢出意味无穷的神韵。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达·芬奇天才画笔的诠释下,它们展现的是人性的深厚情愫和意趣。“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其神秘就在于达·芬奇以一个人物的生动性揭示出人性内涵的无限性。“画是无声诗,诗是无影画。”在人类艺术千百年的诗画之争中,达·芬奇最深刻地理解了两者的冲突,也最深刻地推进了两者的互生。
未完成的“世界之画”
《蒙娜丽莎》是举世公认的达·芬奇最伟大的作品,同时也是无可争议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肖像画。从1503年到1519年,它伴随着达·芬奇生命的最后历程,对这幅“未完成”的绘画,达·芬奇直到最后的岁月仍然在修改它。我们可以说,世界绘画史上,没有一幅肖像画被画家倾注了如此深厚的情感和精力,而且在其生命终结之际仍然没有完成。我们可以相信,达·芬奇的临终忏悔“没有奉献应该达到的艺术成就”,指的就是这幅《蒙娜丽莎》。这幅肖像画历经十数年的持续修改,达·芬奇运用了他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和绘画技术。在综合运用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的基础上,他发明的晕染法,将油画对人物的描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真实质感和生动微妙境界。歌德说:“他(达·芬奇)并不是单纯依赖他天赋中无可估量的才能的内在推动;他不容许任何意外、随意的笔触;一切都必须深思熟虑和精妙极致。从他付出巨大精力研究的单纯比例到他从市井人物中提炼出来的怪异至极的形象,一切都必须同时既是自然的,又是理性的。”正是无止境的追求自然与理性统一的最高理想,达·芬奇创作的《蒙娜丽莎》,不仅是人类绘画史上最伟大画家的艺术结晶,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的生命结晶。在达·芬奇的艺术理想之中,《蒙娜丽莎》必然是没有完成的,因为它是不可完成的。
在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的早期,即1505年前后,年轻的拉斐尔到佛罗伦萨学习绘画,他进入了达·芬奇画室,在临仿《蒙娜丽莎》的基础上,创作了多幅人物造型类似这幅肖像画的作品,其中著名的是油画《抱独角兽的女人》《玛达莉娜·朵丽》和素描《一个女孩》。从此开始,《蒙娜丽莎》为人类肖像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想范式——画中人物与画外观众之间对话交流的形式。因此,肖像画的深刻意义不再是像主的容颜记载或威权张扬,而是一个在画像内外观看与被观看的两个真实个体之间,以人性理想为主题的心灵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蒙娜丽莎》成为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象征和旗帜。依据同时期肖像画的风尚,以乔康达家族的财富和地位,丽莎在画中的服饰应当更加奢华。然而,我们在达·芬奇的画笔下看到是一个更加普通、朴素的女性服饰。显然,达·芬奇要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女性”,而不是一个“富有的女人”。然而,这个女性并没有因为她的素朴而沦入平庸,她普通的服饰不是削弱,而是升华了她内在生命的尊严和秀韵——她是单个的具体的存在,但引人入胜的却是在她直观的真实中包蕴着一切女性、一切个人,甚至自然世界整体最丰盛、最动人的魅力——世界神圣理想的必然本身。这就是“世界之画”。
作为“世界之画”,《蒙娜丽莎》是人类自我表现的“理想的这一个”。她是客观性和理想性的矛盾统一,也是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神妙结合。近500年来,关于这幅肖像画的像主的真实身份,艺术史家列出了一个有争议的长名单,不仅有女性,而且有男性,甚至包括达·芬奇本人。在这个名单中,意大利曼托瓦的女侯爵和文艺复兴艺术赞助人伊莎贝拉,是除丽莎·乔康达之外,最具可能性的一位。达·芬奇在1499年离开米兰后,曾去曼托瓦,作为伊莎贝拉的受助艺术家,居住过近1年时间,而且给她画过一张肖像草图。1500年,达·芬奇离开曼托瓦,返回佛罗伦萨。此后多年间,伊莎贝拉或以书信、或委托代理人,向达·芬奇订购自己的肖像画,甚至给出了“不对画像提任何要求”“酬金由达·芬奇自定”的条件。但是,达·芬奇并没有回应伊莎贝拉的请求。没有文献揭示达·芬奇为何拒绝给这位地位显赫的女艺术赞助人画像。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的是,伊莎贝拉的显赫身份决定了她不是达·芬奇毕生不能完成的“世界之画”的对象。然而,我们又怎能否认,作为“世界之画”,在《蒙娜丽莎》之中闪现着伊莎贝拉的身影和情愫?进而言之,岂止伊莎贝拉,岂止艺术史家争议的那些可能成为《蒙娜丽莎》像主的人物,我们都可以在这幅“未完成”的“世界之画”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并且得到心灵的呼应。
2010年9月16日,我专程自巴黎赴昂布斯堡镇,拜谒达·芬奇生命中最后3年客居的克劳斯-卢契庄园。这是一个秋雨初霁的黄昏,在庄园中,你见不到任何常规的人物雕塑的装饰,整个庄园宛如一座创世之初的伊甸园,全是自然之气。这里有光和暗、有水和土,有千花百草,有禽鸟虫鱼,但仿佛只有一个人。我在连绵的冥想中,回想16世纪瓦萨里在《艺术家的生活》中对达·芬奇的至高礼赞。他如此赞美达·芬奇:“一个人会奇迹般地获得如此丰盛的美质、优雅和才能,以至于他的所有作为无一不表现出超人的神圣,无一不令人意识到他不是人间生物而是神佑的天才。”是的,文艺复兴文化,是人文与技术、艺术与科学、身体与心灵整体统一的文化,做一个“文艺复兴人”,就是要实现在个体中的文化综合的整体性。无疑,达·芬奇正是“文艺复兴人”的至高典范。
达·芬奇被葬于距离克劳斯-卢契庄园不到1公里的昂布斯堡内。目前较为公认的看法,他的墓地在该城堡东南角的圣胡波礼拜堂。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礼拜堂。但今年我重温9年前的拍摄的照片,这个哥特式礼拜堂竟然神奇地出现在照片中。它清晰地伫立在城堡的厚重的高墙上,以俊美的身姿俯瞰着昂布斯堡小镇,在无声地嘱咐着街巷中一代一代来往的人群,“世界之画”,未完成而无限辉煌。达·芬奇在晚年自我抱怨:一幅画都没有完成。是的,世界之画,永远展开,无终无始。
(作者:肖鹰,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转自:光明日报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7254。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