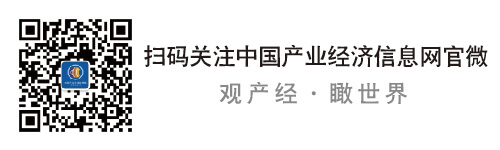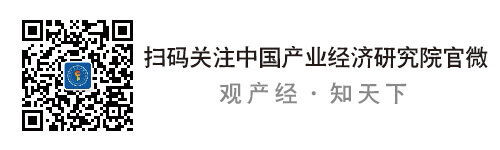从刚刚过去的国庆档电影市场趋向来看,观众对真实事件的兴趣似乎越来越高了。从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到去年的《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直至今年的《烈火英雄》《攀登者》《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祖国》,根植现实、取材生活、还原历史,已经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一种新的叙事策略。
不同于以往单纯完成任务式的重大题材创作,在政策环境和市场规律的双轮驱动下,当下中国银幕对真实题材的把握更多体现出自觉、专业和高效。给人印象深的有三点:一是反应速度。把历史事件改编成电影并搬上银幕速度很快,《中国机长》和《攀登者》等新片从创意筹划、拍摄制作到全片完成,只有短短十多个月。二是类型广度。从军事、科幻到灾难,从登山、消防到航空,所涉领域以往国产片均鲜有踏足,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电影类型化创作空间。三是制作高度。香港导演、内地制片和海外特效技术的三者结合,呈现出较高的成片品质,尤其在表现灾难场面的视觉特效和真人实景拍摄方面,似乎已不输好莱坞。
整体上看,这些取材于真实事件的电影用力脚踏实地,一扫浮躁之风,再现久违的银幕现实主义。从《烈火英雄》《攀登者》到《中国机长》,无论是英雄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演绎、纪实美学的传统回归,还是类型电影的创新制作,都有不少突破,带来了良好口碑和票房。当然,成品并不代表精品,这些影片在内容题材的挖掘、类型叙事的表达以及英雄主题的演绎方面,尚有不少提升空间。笔者认为,历史真实事件的影像表达,关键在于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历史语境和艺术虚构的取舍、行业题材和故事类型的区分、叙事逻辑和抒情张力的平衡。
纪实性:历史语境和艺术虚构
“一个人,一个故事和一个年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策划理念是“吾国吾民”,七位不同风格的导演选取七个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历史瞬间,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这种借鉴国际电影节大师短片集锦的做法并不新鲜,但非常契合国庆档的主题演绎。它的出新在于颠覆了以往献礼片明星走秀的“晚会式”套路,隐喻着创作视角的一个重要变化:由以演员为中心变为以导演为中心,以宏大叙事的大片模式变为短视频创作的短片模式,以重大事件还原的纪实风格渐变为“大事件+小人物”的虚实结合。
虚实问题,是纪实电影表达的首要问题。实际上,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多种不同的取材视角。
于重大历史现场中拆解个体生命体验。《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部讨巧、合时和炫技之作,它较好地处理了焦点和景深。用开国大典、原子弹研发、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航天与扶贫和阅兵检阅七个片段为底色,勾勒以重大事件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历史语境,然后,组织各路人马对这些“核心现场”进行有趣拆解,通过抢险、离散、奇遇和救赎等一系列讲故事技巧,描摹出一组组鲜活生动的小人物,牵引观众走入全民记忆。全片真正的对焦在于唤醒人们潜意识中的集体怀旧,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把历史闪回成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
于再现历史事件过程中重新建构主流价值。《攀登者》是一部具备史诗性构建的电影,面对冰封的历史,它采取了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手法,使主题呈现出复杂多义的意涵。影片取材于1960年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真实事件,并通过艺术性的演绎为观众展现攀登过程中的三层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光荣和梦想”,表现对“中国人的山要中国人去登”的致敬;第二个台阶是“信仰和传承”,表现对“每一代人的使命都高于一切”的攀登精神的纪念;第三个台阶则是“尽职和取义”,表现对“山,在那里”的职业操守的敬畏,从伦理角度探讨“要摄影机,还是要命”的两难抉择,进而叩问牺牲的价值。显然,《攀登者》并不满足于简单还原历史,而是将个人命运置于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攀登的终极意义和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于定格的历史瞬间中全景回溯事件过程。《中国机长》取材于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经历的一段生死旅程,中国机长成功处置飞机风档玻璃脱落的危机,创造了全机11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部幸存的世界民航史奇迹。这个题材固然千载难逢,奈何观众具有全知视角,要让人们猜得到结局,猜不出过程,影片需要解决的是密闭空间内的紧张感、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和角色人物的动作线。编导采取了全程写实手法,遵循类型片的叙事模式,表现空中历险的惊心动魄,对历史事件进行还原。而取材于2010年“7·16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故”的电影《烈火英雄》,视角选取如出一辙。
应该说,历史语境和艺术虚构是纪实电影的一把双刃剑。纪录片《大三儿》的导演佟晟嘉坦言:最大的困境是选择。真实和虚构是“事实的部分”和“部分的事实”构成的对立面。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是纪录片和剧情片的杂糅,对电影创作带来诸多挑战。
第一,尊重历史逻辑。真实性是构筑所有文本的基石,这些真实事件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一部优秀电影剧本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要素。好莱坞深谙此道,很多商业电影都取材于真人真事。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第二,遵从戏剧逻辑。戏剧化是串联故事的纽带,合理艺术虚构是点睛手段,在“日常”和“宏大”之间要落实对接端口,“大国”和“小家”之间要找到情感链接。第三,懂得取舍。香港导演北上带来了商业操作经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隔膜,历史语境不仅指向核心史实的准确,还包含顺应不同的时代语言、地域特征和人物思维方式,对此要剪裁增补,运用合理。总体原则是基于真实,服从艺术,还原现实。
以当下眼光穿越时代迷雾,重建虚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这是一次艰难的致敬,既不能脱离和割裂,也不能囿于复刻和还原。无论借助何种形式和技巧,有一点最为核心,那就是创作者面对历史所持的叙事态度。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一旦进入银幕,就变成了被建构的“历史”。从这点上说,创作者要敬畏职责。
类型化:行业题材和故事类型
当下,中国电影进步的一大标志是类型片走向成熟,如《红海行动》之于军事,《流浪地球》之于科幻,《哪吒之魔童降世》之于成人动画,《烈火英雄》《攀登者》和《中国机长》分别拓展了全新的电影类型:事故灾难、体育探险和空难抢险,把消防、登山和航空这些特殊行业搬上银幕。
当下,观众生活在浩瀚资讯中,不太满足于单向度的灌输,不太满足于大团圆的结局,不太满足于扁平化的塑造,他们对电影讲好故事有更高层次的需求。高品质的类型电影问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商业电影制作规律的认识。
题材和类型。人们对传统电影的认知中,比较重视题材,不太擅长类型,甚至把两个概念混淆。以《烈火英雄》为例,消防只是题材,灾难才是类型。题材包含行业要求,类型涉及故事规则。前者源自革命文学传统,是一个文本概念;后者来自商业电影语汇,是一个运作体系。题材最忌雷同,越抄越乏味;类型不怕重复,越拍越丰富。近年来,海陆空警都推出了代表性的大电影《红海行动》《战狼》《空天猎》《湄公河行动》,市场追逐、效仿的更多是同类题材或创意,并不完全等同于类型片。《中国机长》《攀登者》的出现带来了重要启示:类型比题材更为重要,它反映了中国电影对专业制作人、电影分级制度等一系列电影工业体系建设的要求。对电影文本价值的判断不仅仅只是题材和明星,更重要的是对类型的深度挖掘。
实拍和特效。随着电影工业加速向数码化转型,越来越多的电影制作进入特效影棚,演员也开始习惯绿幕表演,但这终究无法取代实景实拍的震撼力。值得一提的是,国庆档前后的几部大片都选择了真实表演。《烈火英雄》为再现当年新港油罐区火灾,在拍摄现场以1:1的比例实景搭建了港口油罐区,所有演员无替身进入火场演出,画面极富冲击力。《中国机长》按1:1比例定制了飞机客舱,拆成三节,用最新的硬、软件组合制作了3个用电脑操控的运动平台,让机舱可控地颠簸、倾斜、滚动,得以实现电影里驾驶舱、客舱里的真实质感和动态。《攀登者》选择青海岗什卡雪峰进行了集中极寒训练,每位主演都背负17公斤的登山装备,在倾斜度六七十度的雪山学习攀登并实地拍摄。实拍不仅是对灾难场景和抢险过程的全方位展示,更能激发演员塑造真实可感的人物,事实证明,即便在数码特效一统江湖的今天,它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专业和程式。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其成功取决于两个维度。一是从题材的行业属性出发,观众苛求细节的专业性。例如,《中国机长》还原危机的同时,再现了一幅航空业运作全景图,不仅包括从跑道检查、加油加水、保洁备餐、货运分配、安检驱鸟到机组航前检查等一系列严谨工作流程,还包含对飞机本身的性能规格、高原飞行状况、航空公司运行、机场管理、空域调度等一整套复杂的后台管理体系的呈现,《烈火英雄》和《攀登者》同样对消防和登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所展示。一是从类型的戏剧功能出发,要求故事程式化。灾难片遵循“危机-拯救”叙事模式,追求“大起大落”的人物设计,痴迷“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悬念节奏,惯用“平行蒙太奇”的镜头剪辑,为此,《攀登者》增加了雪崩、暴风和冰裂缝等险情,设置了“搭人链、挂铁梯”的桥段。《中国机长》增加了真实事件中不存在的“雷暴云”险情。这些精心设计的灾难奇观,虽为虚构,却符合类型叙事逻辑。专业性和程式化是类型片的两条腿,特定人物的行为处理一旦违背专业性原则,就会感觉“失真”,故事情节的发展演进一旦不按程式套路走,就会导致“失焦”,这是我们理解类型片的两把钥匙。
对当下的中国电影而言,题材日渐丰富,类型还略显单一。例如,航空题材是国外类型片常客,客舱是天然的室内剧场景,可拍成灾难抢险片,刻画英雄;可拍成密室悬疑片,窥探人性;亦可拍成孤岛求生片,叩问内心。而我们对此的演绎尚停留在热血煽情、泪点歌颂层面。技术可以改变和丰富电影的表现形式,讲故事的章法依然是核心能力,为此,有理由更敬畏专业。
英雄主义:叙事逻辑和抒情张力
把真实事件搬上银幕,最难还原的不是火龙,不是雪崩,而是人。大部分经历过生死的英雄,都平平淡淡,而电影要把故事说好,要靠类型吸引观众,靠画面震撼观众,最终,还是靠人物感动观众。《我和我的祖国》塑造了“小人物”的平民英雄,《烈火英雄》《攀登者》和《中国机长》塑造了各个行业中的职业英雄,这些英雄的真实原型的共同特征是“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不是《攀登者》,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国登山队曾经两次登峰的故事。真人真事,尤其是记录历史的电影,其价值表达不仅在于还原事件,还要复刻人物。中国电影的英雄叙事自有其一套内在价值和逻辑。
如何深沉表达家和国。家国情怀是中国式英雄叙事的内核,如同《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一起走”的隐喻一样,《我和我的祖国》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片段:《夺冠》中小男孩冬冬在中国女排夺冠后,涕泪横流的那一句“爸,咱家天线太烂了”;《白昼流星》中深沉的旁白“要是有一天,人们能在白昼里看到夜晚的流星的时候,这片穷土才会被改变”。这些台词背后所隐藏的人文密码,瞬间可以打动国人,这里寄托着我们最深沉的记忆和情感。这些感情并不是空泛的,它要么来自生活中的日常体验,细微而真切,要么来自内心世界的坚定信念,浪漫又含蓄。这是从经过艺术加工的细节中,我们读出的家国——它不只是高高飘扬的旗帜,也是印在路上的浅浅一道辙。
如何定位集体和个人。中国式的英雄主义是立足于更多协作基础之上的集体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表达并不符合东方价值观,国庆档票房飘红,但并没有出现一个“超级英雄”。《烈火英雄》侧重于表现消防员群体,江立伟、马伟国和徐小斌分别率先锋、特勤和远程供水三支救灾队伍在救灾时团队合作。《攀登者》也是多线平行叙事,突击队、大本营和气象组三个团队并肩作战,紧密配合,刻画了以曲松林、方五洲和徐缨为代表的登山英雄群像。最有意味的是《中国机长》,编导采取一种暧昧的策略,全片人物散点透视,事件全景呈现,主角其实是整个川航英雄机组,表现基于集体智慧基础之上的英勇。囿于剧本容量,群戏设计和主要人物塑造经常会发生冲突,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人物的感染力,这两方面如何平衡,依然是编导们要面对的挑战。
如何平衡叙事和抒情。在我们记忆中,塑造伟岸的英雄形象,总是离不开儿女情长。中国电影的英雄叙事结构几乎可以总结成套路:通常以某次危机事件开局,出完片头后,再通过日常化的情景展开故事,其中会针对两到三名主人公以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并线切入或切回,并围绕核心救援主线平行叙事。这是很符合中国人审美传统的英雄观,所谓“铁骨柔情”,只要是英雄,必然有家国情怀的大爱大义。所以,《中国机长》中的英雄机长,一定要赶回家中和女儿庆生,故事才圆满;《烈火英雄》中的硬汉队长,面对火情逼近的绝境,一定会拿出手机,挨个拍下每个消防队员和家人告别的特写;《攀登者》更是精心设计了另一座山,横亘在队长方五洲和气象学家徐缨之间,英雄要攀登的山,被赋予了自然、兄弟和爱人多重人格,角色身上背负了十足的情感张力。
我们看到,叙事和抒情常是灾难现场的一对“难兄难弟”,如若处理不当,在分秒必争的抢险高潮段落,抒情段落的插入,会延宕叙事节奏,破坏连贯性和紧迫感;如遭遇主要人物牺牲,更会在背景音乐和慢镜头所烘托渲染的画面中,让观众嗅到刻意的煽情味道。真实事件中确有无数牺牲,但是,电影的英雄叙事不能总是拘泥于表现悲情,英雄也不总是和绝境联系在一起,真正震撼观众的不是泪,而是我们所面对的未知。英雄主义也不是肉身和口号,而像燃烧的港湾、失速的航班、暴烈的雪峰,包含着对生命的深深敬畏。(金涛)
转自:解放日报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7254。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