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际数学教育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数学的关注。
数学是人类最古老又最活跃的科学,驱动着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发展。在很多人看来,数学很难。它高深、艰涩,难以理解。
但在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蔡天新看来,数学就如同诗歌一般,简练、优美,充满智慧,有时甚至“画龙点睛”。
古老又先进,简练而智慧
蔡天新是一名数论学家,在浙大数学系任教多年。他提出了形素数和加乘方程的概念,后者被德国数学家赞为“阴阳方程”,而有关新华林问题的研究成果被英国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阿兰·贝克赞为“真正原创性的贡献”。
令人诧异的,是他的另一重身份——诗人。
读研期间,“缪斯”女神偶然降临,催发了蔡天新的诗情,自此,他便把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写成了诗。他的诗被印在法国大书店的橱窗上,也印在以色列发行的系列明信片上。
在很多人的眼中,数学代表着理性和严谨,诗歌充满了感性与恣意,两者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蔡天新却认为,数学与诗歌之间向来有着千丝万缕的隐秘关联。
解放周末:在您的理解中,数学与诗歌的关联表现在哪些方面?
蔡天新:数学和诗歌都是最古老却又是最先进的。
数学是自然科学里出现最早的学科,它比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出现得都要早。它诞生于游牧时代,那时人们的主要财产是牲畜。为了计算它们的只数,人们学会了计数,继而学会了加法和减法。
与此相应的是,诗歌是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不过那时恐怕已进入农耕时代,人类已择地居住下来了。由于缺少科学技术和其他手段,为了有好的收成,人们只能祈求上苍风调雨顺,为此需要祷告即念念有词,诗歌因此诞生。
数学之用,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比方说,复数出现几十年以后才在电力学上得到应用;群论发明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被实际应用,但后来在量子力学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都说明了数学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诗歌也是如此。诸多艺术流派比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最早都是在诗歌创作中出现,随后再影响、发展到绘画和戏剧等领域。
诗歌和数学还有一个共同点——简练而智慧。伟大的数学公式往往只有一行字,却能揭示宇宙间的奥秘。李白、杜甫的五言绝句只有短短的20个字,其中蕴含的智慧就足以千古流传。
解放周末:您最近出版的新书《数学与艺术》不仅谈到了数学与诗歌之间的关联,还涉猎了绘画和音乐等领域。为何会做这样的跨界探讨?
蔡天新: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曾对数学和艺术的关系这个主题做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但我留意到,他们似乎更关注数学和艺术的外在形式,比如对称之美(也有的在方法论上做过研究),但从数学和艺术的发展历程来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本质属性,似乎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阐释。
比如,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为什么说17世纪是“天才的世纪”?深入了解并加以研究之后,我发现那确实是一个巨匠辈出的世纪,更关键的是这些杰出的人物都是横跨人文和科学两大领域的巨人。在此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不仅贡献了光辉灿烂的艺术,还引入了透视法、没影点等几何方法,自此打通了文理。而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笛卡尔、帕斯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
我有幸在数学和艺术两方面都做了长时间的实践和探索,所以做了一次这样的尝试。
突破与数学之间的“壁”
1978年,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起轰动。数学家陈景润、潘承洞、王元一跃成为“全民偶像”,引导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
也是在那一年,15岁的蔡天新立志把数学作为自己未来的专业和人生的奋斗目标:他要去潘承洞先生所在的山东大学。
可是,当年的山大数学系在浙江只招收自动控制和电子计算机两个专业的学生,蔡天新只好“曲线救国”,先学自动控制,后在研究生阶段转到数学专业。
15岁上大学、24岁获博士学位、31岁晋升教授,蔡天新在数学的道路上一路前行。不仅如此,他还热衷于普及数学和数学文化。他在浙大和另外4位教授常年开设通识课《数学与人类文明》,出版《数学传奇》《数学简史》等多本书,努力消融人们与数学之间的“隔阂”。
解放周末:说到数学,通常给人一种高深、艰涩的印象,普通人感觉似乎和数学“有壁”。怎么突破这个“壁”?
蔡天新:长久以来,搞数学的人不知不觉地挤在一个小圈子里,里面的人不愿意出去,外面的人也不敢进来,所以我一直在想,身为数学圈内人,能否为数学文化的推广做些实事?于是,我们开设公开课,把受众的需求考虑进去,把文学、史学、哲学、音乐等添加到关于数学的讲述中。后来我也陆续写了一些书,希望能拉近读者和数学这门抽象学科的心理距离。
解放周末:要向公众讲述数学,通常会谈到一位位西方数学家。而您在《数学简史》中为中国古代数学家单列一章,介绍了他们的成就,是否也有一种挖掘“宝藏”的意图?
蔡天新: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数学家中,很多人的“本职工作”是做官,并没有把研究数学作为职业。古代的翰林院没有科学家,皇帝没有意识到科学对于社稷的重要作用,科学家们也没有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即便我国古代科学和科学文化都有所欠缺,仍然有一些亮点在今天不应该被忽略。
比方说,在很多中小学,都有祖冲之的塑像。但实际上,对中国数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家中,比起祖冲之,有一个人的成就要大得多,他就是南宋数学家秦九韶。
有“科学史之父”美誉的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认为,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中国人强调实用,中国数学史基本上是计算的历史,而秦九韶是个例外,他创造了一个定理,即“中国剩余定理”,在许多领域都有重要作用,至今影响深远。还有“秦九韶算法”,在计算机时代特别有用。
在《数书九章》序言的开头,秦九韶便提到,周朝数学属于“六艺”之一。学者和官员们历来重视、崇尚数学。人们因为要认识世界的规律,产生了数学。从大的方面说,数学可以认识自然,理解人生;从小的方面说,数学可以经营事务,分类万物。秦九韶坚信,世间万物都与数学相关,这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不谋而合。
除了精通数学之外,秦九韶还是一位气象学家,我在南京北极阁气象博物馆门口看到他的塑像。《数书九章》中,有一道算题是算雨量器的容积的,证明了雨量器是最早在中国被应用的,西方直到17世纪才开始用雨量器。事实上,他最早定义了降雨量和降雪量。
解放周末:据说,您曾“守护”了与秦九韶颇有渊源的道古桥?
蔡天新: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上原有一座石桥,叫道古桥。道古是秦九韶的字,据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造桥者是秦九韶。后因西溪路扩建改造,原先的桥和溪流成了平地。我在那儿附近住了很多年,后来看到在距道古桥原址约百米处建了一座新桥,我便提议,给这座桥重新命名为“道古桥”,并酌情在桥头设立一块石碑。此建议后来被杭州市政府采纳,我请数学家王元先生题写了桥名。
英国剑桥的数学桥,相传由牛顿设计,是游人的必游之地。所以我特别高兴,在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现在也有了一处科学人文景观。
学数学就是要走遍世界
若是有人向蔡天新抱怨数学抽象、难懂,或许会得到这么一个回答:你知道吗,研究数学有一个方面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数学专业的外语比较好掌握。
这不是一个数学教授的“凡尔赛”。他想表达的是,相对于文科、医学等学科,数学的外语文献没有复杂繁多的词语、语法。数学本身就是一门世界性的语言,学数学的学生因此能更方便地阅读外文书,用外文撰写论文,也有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
而交流,恰恰是蔡天新特别看重并热爱的。这些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了100个国家和地区,工作之余,他还会寻访当地的历史人文和科学遗迹,追随前辈的足迹。
他喜欢行走,并在行走中观察。他喜欢交流,并在交流中思考。他喜欢写作,并在写作中沉淀。
解放周末:您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出于好奇心吗?
蔡天新:有两句话影响了我。第一句是“学数学要走遍世界”,出自数学家哈尔莫斯晚年的自传《我要作数学家》。自小我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认识和探索这个世界是我的兴趣所在,恰好数学专业出国交流的机会较多,我因此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并用心领略了不同的文化。对世界的探索与思考,也反馈到我后来的写作上。
我在《数学传奇》序言中写道:“幸运的是,笔者曾利用各种机会,抵达了书中所写到的每个人物曾经生活过的国度,这使得我对他们的人生轨迹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寻访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伊拉克的巴格达、黎巴嫩(腓尼基)的提尔(毕达哥拉斯的祖居地和数论的诞生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阿基米德的生卒地)、突尼斯的迦太基古城(变分法的传奇故事发生地)、西班牙的托莱多(西班牙古城,翻译时代的中心城市)等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写作。
第二句是“没有表达力的智慧不是智慧”。此语出自法国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眼和心》。小时候我们特别羡慕那些在聚餐时会讲幽默故事的叔叔阿姨,长大后才知道,让人哈哈一笑随后便遗忘的并非真正的智慧,有价值的想法和思想应该用文字表达出来,变成文章或书,有人欣赏,最好是代代相传,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解放周末:您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我们绚丽多姿的生命是由一次又一次奇妙的旅行组成的。即使是最容易让人慵倦的春天,一旦有了计划中的一次旅行,心情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蔡天新:哈佛大学史上唯一的女校长德鲁·福斯特从小有一个梦想,是每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要求可能比她还高些,我希望每年能去一个新的国度。这个想法持续实现了30年,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前,我还和家人去了文莱和苏丹。前不久我去了一次赣州,很有收获。
我觉得,旅行是拓展想象力、提高眼界,并且铸造勇气和自信的很好的方式。通过旅行,跨领域的思考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解放周末:您还曾在国内外十多座城市举办个人摄影展,并应邀在六大洲的数百所大中学校、图书馆、书店做公众演讲。很多人对数学家的想象就是沉浸在数学的世界埋头研究、不修边幅的样子。您觉得自己是“非典型”数学家吗?
蔡天新:什么是“典型”数学家呢?
有些数学家的性格可能确实比较内向,但数学家并不都是不善与人交往的,冯·诺伊曼和罗素就善于交际。人们之所以会特别关注数学家的一些缺点甚至缺陷,可能是因为其中的强烈反差——一个天才数学家,居然如此不善言辞。其实,数学家的个性因人而异,他们的相同点应该是对数学的热爱和执着。
这几年,国内也有未来科学大奖这样的活动,邀请科学家们穿上燕尾服走红毯,引起了社会关注。我觉得,频频上热搜的除了娱乐明星,更应该有那些为社会、为人类带来重大影响的人。我很期待这样的变化。
创新需要远大的志向
尽管走了很多路、去过许多地方,校园,仍然是蔡天新最为熟悉也最有感情的地方。在《我的大学》一书中,蔡天新深情追溯了自己求学时的往事,讲述了一段段与恩师和同窗挚友之间的难忘故事。
大二暑假来临时,蔡天新已基本确定将来跟潘承洞先生做数论,可惜潘老师非常忙碌,少有机会正式授课。“不过,有一次他来听我们的数学分析大课,课后发表讲话,并就课上的一道例题即兴发挥,推导出了更为深刻漂亮的结果。这一高屋建瓴的思想对我很有启发,在我后来自己做研究以及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也都派上了用场。”
对一个人来说,大学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大学生活才有意义?蔡天新有着自己的思考。
解放周末:这个夏天,一批新生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很快就要开始他们向往的大学生活。您有什么心得想和他们分享吗?
蔡天新:希望大家能够保有一种精神气,用良好的精神状态去迎接大学生活。人生是一段长跑,不应该执迷于所谓的“赢在起跑线”。就像体育比赛中,那些一上来就“大杀四方”的球队并不一定最后会获得冠军,反而是那些跌跌撞撞出线、一点点发挥出自己的劲头和实力的球队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在大学里学到多少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大学生活是自我探索和自我发现的过程。找到自己的目标和热情所在,这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宝贵财富,也是让我们“永远年轻”的秘密武器。
解放周末:从各方面来看,现在大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都远优于过去,但大学生们的困惑似乎也增多了。
蔡天新:现在的学生的知识面比我们那时候广多了。我们上大学时使用的教材都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教我们的老师几乎都没有出过国。现在的高校教师大多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在知识的广度和前沿性上更有优势。网络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学生,从小就善于利用互联网来获取知识,有什么疑问也能获得更便捷的解答。而我们当时,只能靠查阅书本资料来获取解答,内容少、过程缓慢。
但如果说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有什么优势的话,可能就是一股坚韧不拔的精神吧。大家都有强烈的对知识、对广阔世界的渴望,都憋着一股劲去学。现在的学生可能就缺少这股劲儿。
解放周末:对于大学生们的新生活,您有何建议?
蔡天新:我常常向我的学生提起剑桥大学的一个社团使徒社。它鼓励拥有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爱好的人每周在一起聚会一次,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讨论。文学家伍尔夫、诗人丁尼生、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都曾是使徒社的成员。
维也纳大学也有个类似的维也纳小组。这是一个由大学教授和个别学生组成的组织,团结有创造性的学者,不限制专业领域。25岁就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而震惊世界的哥德尔,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相比于那些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组成的社团,比如文学社、书画社、篮球社,我建议大家在大学里多组织、多参与使徒社这样的社团,这样的交流可能会碰撞出更激烈的火花,激发出更丰富的想象。我觉得,大学需要这种碰撞,科学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碰撞。
解放周末:或许,碰撞中就会产生创新。
蔡天新:是的,目前的数学研究领域中,还缺少一种鼓励创新和敢于建立评价体系的勇气。大家似乎都特别看重在哪个等级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并把这看作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成绩。
同样,我们很注重解决别人提出的猜想和问题。我注意到,报道某某学者在高影响因子刊物发表文章时,常常在题目上冠以“解决了某某多少年前提出的猜想”等表述。相反,我们很少把提出一个猜想、一个问题或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当作自己的研究目标,所以我还是想强调,创新需要远大的志向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我们要坚定地提倡、鼓励创新。
蔡天新
生于浙江台州,数论学家,诗人、作家,15岁考入山东大学,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学者;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吴大猷原创科普著作佳作奖等;撰写《数学传奇》《数学简史》《数学与艺术》《经典数论的现代导引》《小回忆》《我的大学》等30多部文学和学术著作,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
转自:解放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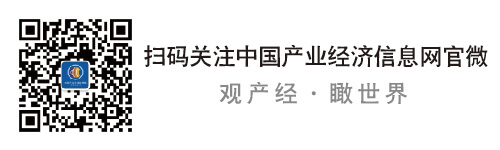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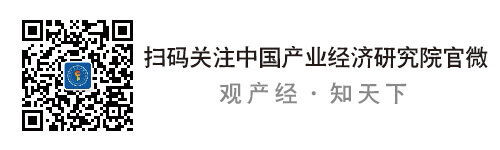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