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吕坤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差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里选取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再命散骑侍郎周兴嗣编纂成文,是谓《千字文》。
作为中国古代三大童蒙读物中的“高阶读本”,《千字文》格式上四字为一句,内容涵盖天文、地理、社会、历史、人伦道德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对仗工整、音韵和谐、文采斐然,被世人称作“绝妙文章”。
它诞生于公元6世纪,却在历史长河中被争相翻译成若干种文字,在各民族中广泛传播。迄今已经发现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满文等多种文字版本的《千字文》。如此众多版本的流行,我们可以想象,《千字文》在中国古代有多火。
西夏人摹仿《千字文》
1038至1227年,党项人在河西一带建立起西夏政权。李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了西夏文,紧接着为了推广新文字,刊布了大量文献,用西夏文大量翻译佛教经典及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还包括学习番汉双语用的《番汉合时掌中珠》。
后来,西夏仿照《千字文》编写字书《碎金》,全称《新集碎金置掌文》,将1000个不重复的西夏文编成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联诗,全诗一气呵成,中间没有明显章节,内容丰富,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顺序明显受《千字文》的影响。
1909年,黑水城遗址出土两种《碎金》写本,可惜被俄国探险队劫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99年,敦煌莫高窟出土的《碎金》残片,行楷字体。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文《大藏经》模仿汉文大藏经的“帙号法”(佛经排架的方法)做法,保留了以《千字文》为帙号加以标注的传统,也就是在每10卷经书题目下分别标“天、地、玄、黄”等字。
丰富而稚嫩的回鹘译本
已知的回鹘文《千字文》残片多达12件,涉及4种抄本文本,分别收藏在柏林、圣彼得堡等地。8至15世纪,回鹘作为游牧民族,主要活跃在漠北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吐鲁番等地,使用回鹘文书写。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部分回鹘部众西迁至吐鲁番盆地,建立起高昌回鹘,他们在这里接触了许多传世汉文典籍,也从汉文翻译了大量佛经。
《千字文》在吐鲁番一带流传甚广,当地一座唐墓里便出土过汉文《千字文》,大约是学生习字本。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一件汉文写本残片,尾题中记录着:天禧年十三年岁次辛未,交河一个名叫胜泉都通的回鹘人阅读了《千字文》。
鹘本《千字文》译者采用直译、意译、音译相结合的方法,甚至为了方便读者,直接在回鹘文中夹写汉字,尽力还原汉文《千字文》的风采和原意。
面对汉语博大精深的语义内涵,译者难免出现失误,如在翻译“微旦孰营”一句时,“微”字古义指“如果没有”,译者却理解成了“小”,这种令人忍俊不禁的错误偶有发生。
用藏文字母标音的《千字文》
敦煌藏经洞所出的杂写类《千字文》多达140余件,其中有一份别开生面的文献,是在汉字的左侧附上了藏文的读音,学界称之为汉藏对音本《千字文》,反映了藏汉之间在语言文化方面学习和交流的深度。
这份残卷从“而益咏”起,止于“徘徊瞻”,存53行,每行13个字,除两行完整外,余均残缺,第2-44行都附记藏文对音。
学者推测它是在11世纪初写成的,当时吐蕃人占据陇右和敦煌,上面的注音应当是操藏语的吐蕃民众为了方便诵读汉字,用藏文来记录汉语的发音。如果我们试着将一组藏文对音用字母模拟出来,可以发现“夫唱妇随”读成了“pu qon bu sui”,这恰恰符合唐代西北方音的发音特点,夫妇读成“pu bu”,说明当时当地的古人尚不会发“f”这个音,而是相对应地发成b或者p,这也是“阿房宫”之“房”读如“pang”的原因所在。
内容齐整、字体纤长的满文本
清代统治者十分崇儒尚道,不仅大量刊印汉文本经史书,还专设翻书房,将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刻印流传。康熙年间,翰林院的编修尤珍书写了满文本《千字文》。
同其他译本相比,此文献的内容相当完整,无汉文对照,字体纤长秀气,颇具美感。其千字不重样的字书意义得以彰显,非常适合用作识字教育,有力推动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民间的传播。
满文本《千字文》后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文献《历朝圣贤篆书佰体千字文》开篇中出现。
1907年,北京振北石印馆印行了《新译蒙汉千字文》,属于蒙古文、汉文合璧,并用满文标注汉字音,后被收录于《清代蒙古文启蒙读物荟萃(全2册)》。
转自:中国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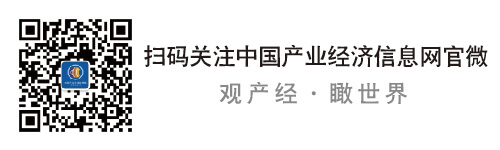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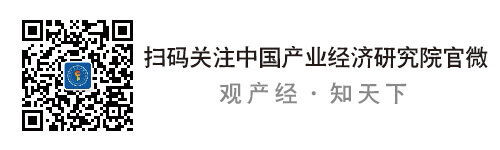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