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谈到贸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那是商人的事情,与民间普通老百姓少有关联。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商业贸易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商贸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河西走廊不仅有“关乎国家经略”的政治意义,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经济意义也是明显的。在长期的商业贸易活动中,河西走廊形成了走廊市场体系和“商贸共同体”。同时,还为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河西走廊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市场贸易把走廊内外地区不同民族的民众长期或者短期地汇聚在一起,实现关联与互动,进而形成一个“多民族命运共同体”。
一、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胡商”
历史上的人群移动是复杂的,其中商业贸易利益的驱动是一个重要因素,相当一部分丝绸之路就是由商人开通的。一般情况下,丝绸之路可分为草原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洋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属于陆上丝绸之路中的链条,而且也是丝绸之路路网中关键性的路段。在一般人看来,丝绸之路是单线的,即便是把丝绸之路看作是复线的,最多也关注的是那几条重要的路线,这其实忽视了丝绸之路最基本的特性。丝绸之路并非单线或者复线的道路,而是由多条主干线路与其他线路连接而成的路网系统。丝绸之路虽然贯穿河西走廊的全境,其实,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群来说,他们所走的具体线路也是不一样的。河西走廊基本上是一条东南-西北方向的走廊,并不是所有从事贸易的商人群体都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进入,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路程之后从最东端走出,或者以相反的方向出入于河西走廊。其实,还有很多的过往客商在河西走廊的南北两端移动,他们从南北的一些端口出入于河西走廊。
早在丝绸之路之前,欧亚草原与中原地区之间就已经出现了文明的交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地区的“胡商”首先进入河西走廊,然后进入中原地区。不过,当时“胡商”进入中原地区也不排除其他的线路。这里的“胡商”指的是西域一带的商人,西域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是欧亚地区的一个文明交汇地带。这里的“胡商”也并非一个明确的称谓,是对来自西域地区的,在体貌形态、语言特征、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中原地区的人们存在差异的“他者”的一个统称。其实“胡商”所指的主要商人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段存在实质性的差异,比如有粟特(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回鹘(突厥)商人等。正是这些“胡商”以及中原地区的商人把西域文明甚至欧洲文明,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地区,同时也把中原地区的文明传入西域和中亚。尤其当中原的王朝国家强盛之时,一些西域国家对来自中原的商人与使节非常友好和热情,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等几乎成为西域地区的宫廷用品和上层社会的奢侈品,西域“胡商”携带汗血宝马、琵琶、狮子等西域“珍奇”进入中原地区。随着丝绸之路上的物品流通,中原王朝的声誉和影响力也在西域地区的上层社会得以提升,在西域不同地段的部族、国家和民众也形成了对中原王朝国家的印象、认识和想象。甚至有些时候,西域地区上层社会的官员可能把其他区域的商人误认为是中原商人而给与一定的“优待”。
曾经有一段时间,“胡-汉”之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二元结构主义”族群认识论谱系成为中原地区辨析“他者”与“自我”的重要标准。其实,由于“胡人”群体本身是由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多个民族的人群构成,“二元”的核心是多元。在中古时期的汉文典籍中出现了“胡椒”“胡麻”“胡笳”“胡琴”“胡乐”“胡舞”等大量关于“胡物”的记载。其实,这些加了“胡”字的物品未必全部来自被看作“胡地”的西域地区。中古时期还出现了对“胡人”形象的描绘,最典型的就是敦煌壁画中出现的一些“胡人”画像。这些画师可能接触过“胡人”,也可能“胡人”画像是纯粹出自画师的想象。总而言之,在中古时期谈论或者书写“胡人”似乎成了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在有些典籍与图像中则可能出现对于“胡人”的误读,这也体现出了古人的族群边际意识。总之,我们从这些历史典籍与图像留存中发现,当时关于“胡人”的形象既显示了一种“胡”“汉”之间的边界,也体现了一种“胡-汉”二元一体的多民族观念。即便是一种通过想象而建构的族群观念,也意味着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非单一性”的多民族意识。
在中古时期出现的“胡人”不仅仅指的是某一个族群,而是一个分布地域广泛、民族成分复杂的群体,包括西域、中亚、西亚、欧洲,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群。“胡人”意识是当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意识,在其背后突显的是中原王朝国家强盛与开放的态势、发达的商业贸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域内外”互动交流机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把作为“胡人世界”的欧亚大陆上所属不同文化的人群,与中原王朝国家关联在一起,丝绸之路充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地段或者链条,也关乎丝绸之路的繁荣和通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塑与构筑过程极具意义。
虽然河西走廊的长度对于整个丝路而言微不足道,但它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西走廊对于世界贸易体系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原文明和域外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发挥过显著作用。
西域作为“文明十字路口”,世界上的诸多文明类型汇聚于此,河西走廊犹如西域地区东段的一个“瓶颈”,是西域文明向东传播的一个重要通道。正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在河西走廊上出现了西域文明进入中原地区或者中原文明进入西域的多个中转站。在有些历史时段中,河西走廊是“胡商”的云集区域,如《甘州府志》所载,隋炀帝大业年间,“尚书左丞裴矩驻张掖,掌交市。帝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当今在河西走廊境内的焉支山一带,还出现了关于隋炀帝时期“万国博览会”的传说。即便这是一种当地人的“历史心性”,将隋炀帝派朝臣接见西域多国商人作为一种历史资源来充实文化产业,其背后也说明了河西走廊与西域之间的地缘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商贸活动的可能性。粟特商人是“胡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古时期粟特商人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很多聚落。根据荣新江教授的考证,一位粟特康国上层社会的官员曾担任“甘州刺史”一职,敦煌(古称沙州)、武威(古称凉州)曾是粟特人的大本营,武威曾经也是粟特人的一个贸易集散中心。河西走廊不仅仅是一个陆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在丝绸之路贸易中还充当了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过渡带。走出西域地区的“胡商”群体,有时候在河西走廊滞留一段时间,把西域文明传播到河西走廊之中。
河西走廊处于地理上的咽喉地带,丝路上的商贸队伍一旦绕开河西走廊,进入北面的蒙古草原地区会面临大戈壁和沙漠,水资源匮乏,走南面则进入青藏高原,复杂的地形影响商路的通畅,高寒的严酷气候影响商人及载货牲畜的生存。相较河西走廊以南及以北区域而言,河西走廊的海拔相对较低,地势平坦,水资源充足,绿洲城镇上还设有驿站,这些条件满足了商队的基本需要,还为丝绸之路的通畅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一直在延续。历史上,当河西走廊出现割据政权,丝绸之路往往会“绕道”或“改道”,选择草原丝绸之路等,丝路上的商队可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情况下,河西走廊也会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一个“死角”,只能等待政治格局的变动与丝绸之路的重新启动。明朝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严重削弱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河西走廊的商路相应地也明显沉寂了很多。然而,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完全中断,西北地区由于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海岸,一些商品还是在陆上丝绸之路上流动着,也有域外的商人携带商品从陆上丝绸之路出入于河西走廊。
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商人的流动,促成了中原商人与“胡商”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丝绸之路牵动着跨区域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也是历史上铸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途径和载体。作为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组成部分的河西走廊,对于商业贸易中多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商贸成为区域文化的“连通器”
商业市场往往是文化汇聚之地,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中,商贸活动和商人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河西走廊地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新疆绿洲、黄土高原这四大地理板块之间,相应地,河西走廊也就在这些区域文化的“包围”之中。以上文化区域的相应边缘一旦稍有伸张,其文化元素就会直接进入河西走廊。通过商业贸易,河西走廊把周边“四大区域”的文化连通起来,实现了多重文化的汇聚和交融,同时又向周边区域进行辐射。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对于“四大区域”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河西走廊本身所产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这首先就在于河西走廊是否有一定规模的市场,以及其供应的农业产品能否满足周边地区畜牧社会的需要。
有些规模比较大的市场是由王朝国家的相关上层机构直接设定的。例如,明、清王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大型的“贡市”与“互市”,吸引了来自新疆天山一带、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区的大量各族商人到河西走廊开展贸易活动,内地商人亦携带农耕产品涌入河西走廊,满足了各方商人的商贸需求。“朝贡体系”是历史上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地区之间建立的政治秩序体系和互动系统,其中商贸互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物质基础。如地方文献所记,明弘治二年(1489年)从中亚撒马尔罕运来的贡品狮子等,进入了作为中转站的河西走廊的张掖(古称甘州)一带准备运往皇都顺天府(今北京)。
农耕与畜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要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两种文化类型,二者之间属于互补型关系,尤其体现在各自都需要对方社会的产品,因此商业贸易是实现二者互动的最基本形式。就河西走廊周边区域来说,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基本上属于畜牧社会,天山以南的绿洲多属于农耕区域,但天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属于畜牧社会。因此,河西走廊的绿洲农耕社会就嵌合在三大畜牧社会之间,畜牧社会所需农业产品的供给就由河西走廊的市场优先承担了。历史上,河西走廊内部的绿洲社会生产一些农耕产品,比如粮食等,但远远无法满足周边畜牧社会的消费需求。不仅是粮食,畜牧社会所需的大量布匹、茶叶、铁器、瓷器等物品,都需要从内地运往河西走廊。可见,对于周边大范围畜牧社会的需求而言,河西走廊的市场更类似于跨区域商贸网络的中转站。支撑河西走廊的畜牧-农耕商贸的,是一个庞大的农耕社会,其范围从黄土高原的关陇地区到中原腹地,甚至延伸至江南地区。这些农耕区域的产品进入河西走廊,再于此中转,流入周边的牧区社会。当然,河西走廊的市场网络也无法完全满足如此大范围的畜牧社会的需求,进入以上这些畜牧社会内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商贸通道。
蒙古高原位于河西走廊的北面,其西南面的部分地区与河西走廊相接壤。当前作为蒙古高原组成部分的阿拉善高原,与河西走廊的民勤、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区相连,河西走廊有多条进入蒙古高原的通道。孙明远、王卫东在本专栏文章《河西驼道最后的骆驼客》中指出:“18世纪中叶清军平定准噶尔部以后,从中原经由河西到达边疆地区的商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河西走廊过星星峡到新疆,被称为甘凉大道;一条是经河西走廊东端沿石羊河而下走阿拉善高原,往西过额济纳到新疆,往东到绥远、包头、张家口直至北平、天津卫,称北道。”特别是在驼队盛行时期,民勤一带的驼队极具典型性,其向四周呈网状分布,来往于农牧区之间。驼队的商贸运输勾连起庞大的商业网络,河西走廊内部的绿洲城市、周边区域的大城市,甚至内地的大城市都在其中。如此,有大量的农耕产品从河西走廊转入蒙古高原,蒙古高原西南端部分地区的畜牧产品的一个重要流向亦是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地区。河西走廊成为农耕商品与畜牧商品的一个中转站。
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畜牧社会,尽管其内部也出现了大量出售农耕产品的市场,河西走廊作为中转市场对青藏高原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的河湟地区,与河西走廊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在祁连山脉南北麓之间有一些通道,部分通道还是历史上重要的“商业大道”,其中扁都口最具典型性。扁都口在文献中有“大斗拔谷”的记载,蒙古语的意思就是“险要的关隘”。明、清时期,扁都口是从河西走廊进入青藏高原的一条商业主干道,大量来往于河湟地区与河西走廊之间的商人和牧区的牧民,通过扁都口在牧区与农区之间穿梭,进行着商业贸易或者个体性的产品交换。由此,扁都口不仅对于丝绸之路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实现了青藏高原牧区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关联。在河西走廊的东段,祁连山南北麓之间出现了一些“密集型”的通道,对于来往于这一带的商人来说,即便对一些小道也是“轻车熟路”。河西走廊的农耕产品沿着一些通道进入青藏高原,同样,河湟地区的一些畜牧产品也从当地的市场流入河西走廊。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庄浪(永登)、凉州、甘州、肃州与青藏高原的西宁、丹噶尔等城镇之间形成了商业网络,河西走廊的一些城镇成了商业网络当中的节点,把青藏高原与天山一带的游牧社会连接在一起。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的城镇之间形成的商业网络体系,也接通了畜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地处“农耕-畜牧”过渡带的河西走廊,商业网络的形成以及通过商业网络的文化互动是一个重要特性,在其背后也就是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互补性的连通与互动。河西走廊西段的党金山口也是河西走廊通往柴达木的一条商业通道。这些重要的商道把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甚至还是连接中原地区、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重要商路。
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是两大畜牧文化体系,河西走廊正好处于二者之间,在历史上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文化互动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自1247年“凉州会盟”以来,伴随着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政治互动的是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多民族的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
天山北部地区属于畜牧社会,需要大量的农耕产品,但天山南部的农耕产品还是无法满足畜牧社会的需要,更多的商品还是需要从内地输入。于是,明、清时期,在河西走廊出现了一些定期和不定期的市场,这些市场吸引了天山北部地区的蒙古人、哈萨克人、布鲁特人(柯尔克孜人)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商人。这些市场的设立不仅实现了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还为天山南北地区与中原的人群接触与交融提供了保证。
地处不同文化区域边缘地带的河西走廊,其联动起来的跨区域商贸网络,使得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商人和民众进入河西走廊的市场,实现了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民众对于“异文化”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建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场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民族共同体。
三、绿洲市场的商贸网络与民族互动
河西走廊的平原地带主要由绿洲和戈壁构成,再加上少量的沙漠。适应耕作的土壤与河西走廊的三大内流河水系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河西走廊历史上碎片化的绿洲。从明、清直至现代,河西走廊的绿洲面积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在一些戈壁地带还开发了一定规模的农田。这样,河西走廊碎片化的绿洲也就形成了绿洲连缀体。河西走廊的绿洲分布格局,相应地形成了河西走廊的绿洲商业贸易格局,并进一步形成绿洲贸易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河西走廊上绿洲面积的大小不同,走廊东段、中段、西段绿洲城市的规模亦不同,而城市规模和绿洲面积之间关联紧密。发展到今天,河西走廊的绿洲分布格局已经与历史上有了较大差距,这种绿洲分布格局及其内部的交通道路体系的变迁,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河西走廊绿洲贸易体系。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曾基于中国四川有关城镇与村落的调查,提出了“市场理论模式”,探讨村、镇分布格局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范式。这一“市场理论模式”应用到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中、东部地区依然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在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带以及绿洲市场格局中,“市场理论模式”出现了部分的“失灵”。首先,地理环境不同,市场体系也就存异。四川成都平原地势平坦,可耕作土地相对集中,人口密集。而历史上,河西走廊上的不规则绿洲散布在戈壁中,其人群聚落也与成都平原的聚落有较大差异。在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模式”中,集镇并非是均质化的,在大、小集镇之间还有过渡性的集镇。而在河西走廊的大集镇与小集镇之间,并未有明显的过渡性集镇,小集镇有一种均质化的趋向。河西走廊集镇的规模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看是否位于绿洲的中心地带,在历史上,武威、张掖、酒泉等城市内部都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市场;其次看是否地处交通要道,特别是农耕社会与畜牧社会的交接地带或者交通要道的出入口附近,比如在清顺治年间,今古浪境内的大靖、土门,以及距扁都口不远的洪水,曾“开市于此”。
河西走廊的绿洲社会是不成规模的“亚绿洲”或者“次绿洲”。每个绿洲内部都有其市场体系,包括了多个不同层级的、大小不等的市场,形成了绿洲商贸圈。大体上,商业贸易规模与绿洲面积呈正比,面积较大的绿洲供养着更多人口、聚落和城镇,也形成了规模更大的行政机构与贸易体系。
事实上,当下河西走廊的市场格局与历史上的市场格局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就规模来说,当前的市-县(区)-乡(镇)三级行政结构大体上对应着规模不等的三级市场结构。由行政规划结合市场本身的发育,过去没有市场的地方形成了市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出现了集市,而有些曾经商旅云集的重要市场地位不再。在今日的河西走廊上,有些地方市场以“旬”为单位设立集日,每月仅3个集日,这与甘肃中、东部地区高密度的集日形成了显著差距。在日常生活中,民众经常去哪个集场主要取决于从村落到集市的距离。基层集市通常设置在政府所在地,大多处于多个村落的中心。其中具有地缘关系的几个集市形成了“集市集群”。曾经有一段时间,部分行商游走在不同的集市上,或者在特定的“集市集群”中从事贸易活动。一些有实力的商人会从基层的集市进入更高级别的市场。
对于河西走廊绿洲内部的市场体系而言,周边牧区社会的介入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支撑性因素。正因为河西走廊绿洲的周边区域是大规模的畜牧社会,才使得河西走廊绿洲内部的市场贸易有了一定的规模。历史上的商贸形式一度有“在邑钱,在野谷”的分类,即在农区市场上是货币交易,在牧区是物物交易,粮食是农区商人携带的主要商品。上世纪50年代之前,在畜牧社会物物交换的贸易形式也是很普遍的,通常外来商品在牧区社会的价格可能远远高于其在农区社会的市场价格。
笔者这几年在河西走廊进行调查发现,历史上很多牧区社会的各族民众在农区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关系和熟人网络,最基本的方式是通过“干亲”这种拟亲属关系。这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朋友圈是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河西地区的汉人社会有一种普遍的民间认同,认为孩子要想健康成长,就要结“干亲”,有时候还会结好几个。人们还认为,如能结到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干亲”,对孩子更吉祥。这种对“他者”的文化认同背后,其实还蕴含着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有些跨民族之间的交换行为就发生在双方的家里。很多时候,不管是在市场还是家庭内部的交易行为,都建立在农区社会和牧区社会以“干亲”为特色的朋友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河西走廊的绿洲市场贸易,为以河西走廊为支点的走廊内外多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互动提供了场所,也对农耕区和畜牧区“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河西走廊内部不但形成了商业网络,而且河西走廊还起着“联动”作用,把周边的广大地区纳入更大的互动网络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西走廊具有商业“中心”地位的意义。设立在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市场,吸引了河西走廊内部及其周边牧区社会的多民族民众,甚至是远道而来的大量各族商人。河西走廊的绿洲商贸网络促成了多民族的深入互动,进行商品贸易的不同民族不仅在“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中建立其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也共同促成了各民族互通有无、命运相连的意识。河西走廊的贸易体系形成了一个多民族互动网络,这一网络既是一个商贸共同体,又是一个多民族命运共同体。
【作者:李建宗,系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北民族走廊、区域社会研究。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青海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2017-GMG-023)和青海民族大学高层次人才(博士)项目“西北民族走廊的族群流动与文化流通——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的关联性研究”(项目编号:2018XJG03)阶段性成果。】
原标题:走廊市场体系与“多民族命运共同体”
转自:中国民族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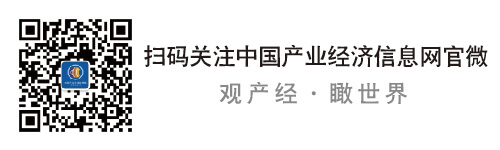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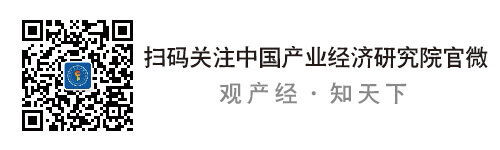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

版权所有: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京ICP备11041399号-2京公网安备11010502003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