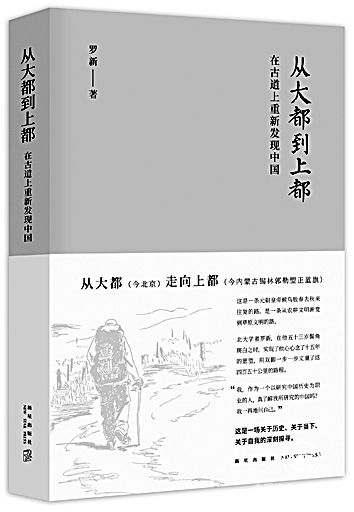黑河旧桥吴黛君绘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罗新著新星出版社
游记写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上起六朝《兰亭集序》《洛阳伽蓝记》,下至明清《徐霞客游记》《登泰山记》,都是国人熟悉的经典作品。在古人的精神世界里,游记大抵不离山水之念及隐逸之思。进入20世纪尤其是现代白话文流行后,游记开始突破古代游侠、游仙式单一写作格局,呈现出比过去复杂多面的书写特征。今天,游记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体裁,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普遍的记录与分享形式。
然而,回顾20世纪以来的白话游记史,真正写得好看、耐看、可以反复看的作品却不那么多。2017年年末,有一本旅行文学的出版令人十分喜悦——《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这本书写得像小说一般精彩好看,像诗歌一样浪漫深沉。其精神世界完全属于现代,文体结构中西同冶,所表达的新境界,示范的新形式,为旅行游记和历史散文写作结出的一枚真果实。
“游记里满是梦”
学者纪游往往易伤两病:一为拘泥,一为轻浅。前者风格精粹凝重,但有时令读者感觉空间紧张,腾挪局促;后者虽自有一种朴实亲切,然流水账终究距学人本色甚远。而在《从大都到上都》里,以上两病均得以不同程度收治。一边是史学家思连千载,一条辇路古今对接,态度庄重又恳切;一边是徒步人神鹜八极,飘忽游荡,仿佛迷离失向桃花源。“这是到了哪儿!”读者惊呼,继而拍手,“啊,原来还可以这样写!”无怪朱自清曾感叹,“游记里满是梦”,反省自己早期《欧游杂记》“无我”式记行,游梦无踪。
像梦那样放纵,又像梦那样剔透。看上去东跑西窜,肆意无理,其实流转有序,收放自如。作者自白,爱读西方游记,尤其是英人游记。果然得其精髓,且随物赋形,槛外风光更上层楼。例如那位看上去因一个偶然电话被插叙转镜的隐没青年,一处因随机小憩被记忆回澜的粉蓝色牵牛花……仿佛一场精心控制的即兴,埋伏着旧日激情里不曾熄灭的火焰。
此外,还有那些闲笔。诸如沿途详细汇报自己充饥的详情,小店里无意中听到的一串冷调对话,因不敢看同伴脚伤遂兴致勃勃围观路边打牌人……这些段落似乎该回应契诃夫法则:“在第一幕中出现的枪,在第三幕中必然会发射”,删除为宜,但想到九叶诗人郑敏的论述:“素材要变成诗的内容必须经过一次艺术观、灵感、想象对它们的发酵和催化。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就呈现在某种逻辑的安排里,这时结构就诞生了。”这才是符合本书运思匠心的妙义箴言啊!
不必再羡慕英语旅行文学世界里漫游的读者,现在,在这个汉语的梦境世界,我们也可以开心地浪游,幸福地“迷失”了。
忧思与担当
“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像是把包裹忘在了别处,也像是自以为被人盯了梢。过于宽松的衣装让他显得很虚弱。鼠灰色的华达呢外套耷拉在肩上,皱巴巴的……”这是英语旅行写作名家保罗·索鲁在他横贯欧亚大陆的游记《火车大巴扎》中描述的首位所遇乘客。此时,在这儿,《从大都到上都》要和许多西方旅行书写分手了。来看看我们将要在本书里遇到的一个途中场景:“迎面嘚嘚嘚的过来一辆黑驴拉的板车,车上装着两袋化肥,赶车人侧身坐在车首,上身是污黄的白衬衣,头上扣着大草帽。与我们擦身而过时,他的眼睛藏在暗影里,我却分明感觉到他深深地凝视。”
保罗·索鲁宣称,“游记对作家自己内心世界的揭示胜于对所描写的地区的揭示。”对应他的刻薄疏离,作壁上观,《从大都到上都》充满对普通人尤其是边缘人的温情注视,目光理解之真,感受之挚,婀娜柔软,刚健清新。在近日接受的一次新书访谈里,这位历史学家说道:“今天的历史学者应该关心边缘人,夹缝中的人,有责任发掘过去我们以为不存在的关系、情感、意志……”
“我像一张光的网,撒向你”,还有你身边,那热情洋溢的小狗,悄没生息溜过的小猫,偏头似要打招呼的黑驴,水草间抬头趋步的骆驼,以及花瓣的甜香,风在草丛涌动的声音……
个体而外,本书也展现出一位历史学者的整体性当代关怀。田野里的土豆与一国主粮政策、富国强兵与普通人的生活关联……忧思自然深广,既是学者书斋研究本业的回响,也是现代国民公共领域的自觉承担,一如微博上那个12万粉丝的账号——历史学家“罗新PKU”。
行走中的书写
1890年夏,契诃夫前往北太平洋上的政治犯流放地萨哈林岛,三个月后回来,以“诗歌的精确和科学的激情”,写下伟大的非虚构游记《萨哈林旅行记》。在人类学研究的初期,游记曾经是重要的知识与经验来源,田野志向亦被视为当然寄托。今天,这种要求是否早已经淡去?
阅读《从大都到上都》,遗憾有时会在某个时刻袭来——“贾先生送我们到靠近大门处,指着谷地里的村庄说,村里有古庙,去看看吧。因为要赶路,我们并没有进村去,听说村里还有古戏台,大概街道布局也是旧的,可惜我们只能从村口往里一窥,只见到窄而深的巷子”。徒步行走,全程依靠双脚,“赶路”兼程以如期抵达,似乎理应比沿途所观,更为紧要和迫切。且和乘坐交通工具比起来,行走还是那么的疲惫消磨:“行走的速度越来越慢,每天抵达目的地的时间越来越晚。即使偶尔早到,也困乏得无力读书,笔记只记得寥寥数行,完全与计划不沾边”;“今天睡意来得特别早,拿起笔记本,只写得几行字,就关灯睡觉。”
行走与书写,究竟该谁凝视谁?谁成全谁?
还是,要像这首法国中古游吟诗任意的歌唱?
“我要做一首歌纯粹什么都不是
既不关于我也不关于任何人,
不关于爱情或青春年少
或者任何什么。
它来到我心里在我熟睡着
骑着马的时候
…………”(曾英)
转自:国学网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