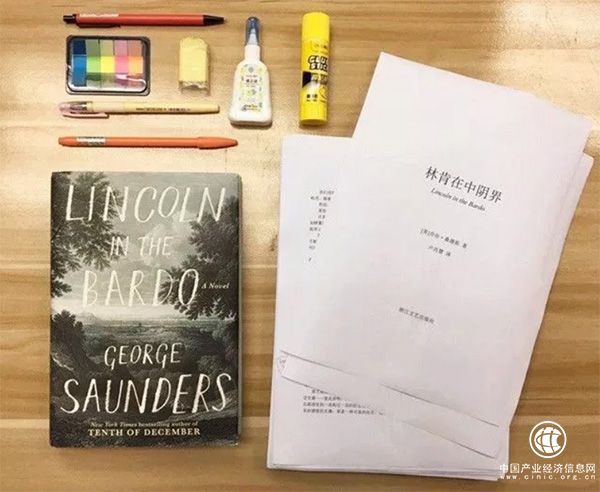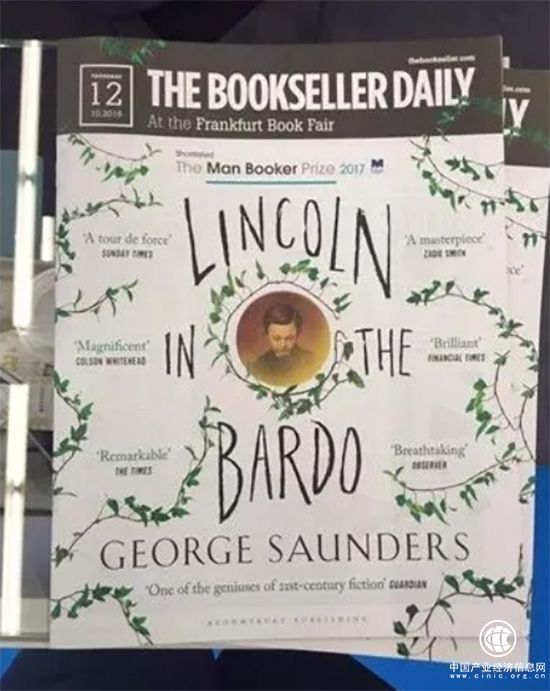编者按:伦敦当地时间10月17日晚8时,现年59岁的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GeorgeSaunders)凭借《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intheBardo)获得2017年英国布克奖。
目前本书中文译稿已经完成,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于年底前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刊载《林肯在中阴界》(节选)试读。
译稿就位
我们成婚那日,我四十六,她十八。这下,我知道你会怎么想了:年纪大得多的男人(不瘦,略秃,瘸着一条腿,几颗木牙)行使婚姻特权,因此让那可怜的年轻妻子受辱——
然而,错矣。
那恰是我拒绝做的事情,你瞧。
在我们新婚初夜,我拖着重重的脚步走上楼,因为醉酒和跳舞脸色泛红,发现她穿着件轻薄如蝉翼的什么东西,是她一个姑姑硬逼她穿上的,丝绸衣领随着她的颤栗而轻轻抖动——不能那么干。
我温存地跟她说话,我告诉她我的真心:她美丽;而我,老,丑,且心力交瘁;这段婚事是不配的,不是本着爱而是为了利;她父亲穷愁潦倒,她母亲患着病。这就是她在此地的缘故。我对此非常明白。当我看出她的害怕——我的措辞是“厌恶”——时,我说,并不会奢望去碰她。
她向我保证说她并没觉得“厌恶”,尽管我瞧见她那张(清纯的,双颊绯红的)脸因为说谎而扭曲。
我建议说我们应当做……朋友。任何事情,都应当不藏不瞒,就像我们已经圆了房那样。她应当轻松愉快地在我的家里过日子,努力把这里当成她自己的家。而我则会对她别无他求。
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们成了朋友。亲密的朋友。没别的。然而,那却又是那么地丰富。我们一起笑,一起决定日常起居的事情——由她帮着,我事事更替仆人们着想,跟他们说话也不再那么潦草打发了。她趣味高雅,成功地完成了室内装修,而花费却只是预期开销的一个零头。我每每踏进门时,就看见她快乐起来;我们讨论家居事务时,我发现她会侧身向我靠过来;我简直无法说清她是怎样地改变了我的人生啊。我很幸福,够幸福的了,但现在我常常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低声祷告,就是这样:愿她在此地,愿还在此地。就仿佛一条哗哗奔涌的河自己取道流过我的家,家中如今充满水的清新气息,我总是意识到有某种慷慨的、自然的、激荡人心的东西在身边流淌。
一天晚餐时,她在我的一大群朋友面前,竟主动地对我赞美了一番——说我是个好人,体贴,睿智,厚道。
当我们四目相对,我看出来她说的是心里话。
《林肯在中阴界》在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
翌日,她在我的书桌上留了一张签条。尽管羞涩阻止了她用语言或行动表达这份情思,签条上这么说,我对她的宽厚,产生了心有所望的效果:她很快乐,在我们的家里,她确实相当安适自在,并且渴望,她是这么写的,要“以彼此亲密无间的,于我,尚为陌生的方式,拓展我们俩共同幸福生活的新疆域。”她要求我在这件事情上引导她,就像我在“其他诸多方面引导她进入成年世界”那样。
我阅读完签条,便去用晚餐——看见她相当光彩焕发。在仆佣面前我们彼此交换了坦诚的目光,对我们俩从这无望的情形中设法替自己找到了希望感到欣喜。
那天夜晚,在她的床上,我很审慎,保持自己惯常的风度:体贴,殷勤,恭顺。我们只是浅尝甘露——彼此亲吻,拥抱——不过请你不妨想象一下,这突然降临的纵情欢爱的醇美。我们彼此都感觉到一浪高过一浪的欲念之潮的冲击(是的,当然),不过靠着我们缓慢而牢固地建立起来的感情的支撑:那是一种可靠的结合,经久而真实。我并不是没有经验的男人——小时候很野;在弹子巷、棒球场、恶狼窝混过很长时间(这么说,相当不好意思);曾经结过一次婚,而且相当正常——然而,这情感竟如此强烈,在我,全然不曾有过。
我们彼此心照不宣的是,次日夜里,我们将继续一同更深入地探寻这片“新大陆”,早晨我好不容易抵御那拖住我、挽留我在家的强大引力,去了我的印刷坊。、
然而那天——哀哉——就是那梁木之日。
是的,是的,厄运!
一段梁木从天花板上落下来,就砸在我这里,我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因此,在我康复期间,我们的计划非得推迟不可。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躺入了我的——
一种所谓的病匣,被认为——认为是——
【汉斯·福尔曼】
疗效甚佳。
【罗杰·贝文思三世】
疗效甚佳,是的。多谢多谢,老兄。
【汉斯·福尔曼】
不胜荣幸。
【罗杰·贝文思三世】
在起居室内,我躺在我的病匣里,感到相当荒唐;就是这间起居室,我们新近还(快乐地,忐忑地,她的手握在我的手中)穿过它,去她的卧房。接着,那位医生回来了,他的助手把我的病匣抬上他的病辇,于是乎,我就看出来了——我看出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无限期地推延。真令人烦恼!现在,我什么时候才能领略婚床的全部愉悦与快感呢?我什么时候才能阅尽她的赤裸之玉体呢?什么时候她才会,那渴欲的嘴,那绯红的腮,那样地凝视我?什么时候她能放浪地松开长发,让它最终缠绕我们的身体?
啊,看来我们非得等到我完全康复。
这情形实在令人烦恼。
【汉斯·福尔曼】
然而,或许,忍耐是金。
【罗杰·贝文思三世】
不错。
当然我承认,当时我心里并不这么以为。当时,在病辇之上,还没封盖,还能松动,我发现自己暂且可以离开那病匣,跳将出去,踢起一股小小尘土,甚至还撞碎一只花瓶,一只在起居室里的花瓶。但是我的妻子和那医生正专注地讨论着我的伤情,竟没注意到。我简直不能容忍。我承认,还发了一通火,引一头熊闯进狗的梦里,吓得那几条狗唁唁大吠,在他们中间乱窜乱跑。那会儿,我还能那么干!那些日子啊!现在我可干不了了,既无法引一头熊走进狗的梦,也没法领我们这位沉默的年轻朋友上馆子!
(他看上去的确年轻,是不是,贝文思先生?从他的外形来看?从他的姿势来看?)
不管怎么说,我回到了自己的病匣,就像以前那样哭啊哭——年轻的朋友,你明白这事了没有?当我们新到这片病苑,年轻的先生,感觉直想哭,接着发生的是,我们渐渐变硬起来,关节部分有种轻微中毒的感觉,体内那些小部件破裂了。如果我们新鲜,我们也许还会屙几团屎出来。这就是我干的,那天一路出来,在病辇上:我趁新鲜之际,在我的病匣里,就屙了几团屎,出于愤怒,结果怎样呢?我就一直守着这坨屎了,而且,实际上——我但愿你不介意我的粗鲁,年轻的先生,或者可恶,我希望这不会有损于我们之间初萌的友谊——这坨屎至今仍在下面,此时此刻,在我的病匣之内,虽说干硬了许多!
天啊,你是个孩子吗?
他是孩子,是不是?
【汉斯·福尔曼】
你既然这么提到,我相信他是的。
看,他来了。
几乎是饱满的身体啊。
【罗杰·贝文思三世】
我深感歉疚,我的上帝。还是一个孩子,就困囿于一口病匣之中——而且,还得听一个成年人陈述他那病匣内一坨干屎的种种细节——这委实不是,呃,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进入他的新,呃——
一个男孩子。还只是个小孩子。噢天啊。
深感歉疚。(乔治·桑德斯卢肖慧)
转自:澎湃新闻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