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达(1914—1997),中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和实践者。他于1932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毕生致力于重新发现中国古代建筑学体系,并尝试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确立自成体系的中国建筑理论。他著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尤以宋《营造法式》专项研究享誉中外。
近日,《陈明达全集》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向读者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人形象。在出版之际,20年来一直整理陈明达学术遗产的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丁垚教授接受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的专访,“陈明达建筑学术的最大特点还是关心建筑设计,当然,这也是建筑学术的基本特点。如果排除掉时代性的差异,你会发现陈明达的研究和梁思成是很像的。”
陈明达,湖南祁阳人,1914年12月25日出生。1932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1953年,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局(今国家文物局)工程师。1961年,任文物出版社编审、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97年8月在北京病逝。
1930年,高中毕业后,陈明达打算赴东北大学在梁思成先生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建筑系读书,后因经济原因辍学谋生。1932年,经莫宗江介绍,陈明达入营造学社工作,师从梁思成、刘敦桢学习中国建筑史。1935年,陈明达与莫宗江等在中国营造学社读研究生。
中国营造学社当时分为“法式组”与“文献组”,由梁思成与刘敦桢分别负责。在实际的古建筑调查中,两组既有分工,又常常合作,莫宗江为梁思成主要助手,陈明达为刘敦桢主要助手。陈明达跟随刘敦桢先生测绘调查了大量古建筑与石窟寺,参与测绘古建筑百余座。如:1934年,调查河北定县、易县、涞水等地古建筑;1935年,考察河北西部八县,考察古建筑三十余处,测绘北平护国寺,调查北平六处喇嘛塔;1936,赴河南调查汉阙、少林寺初祖庵、嵩岳寺塔、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以及1938年至1943年西南地区的古建筑、石窟寺、墓葬遗址等。而中国营造学社留存至今的大量图纸,很大一部分都出自于莫宗江与陈明达之手。
1938年至1943年,陈明达参与了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展开古建筑调查研究。陈明达全程参加了四川汉代石阙考察,并代表中国营造学社参加“国立中央博物院”组织的汉代崖墓发掘工作,撰写完成论文《彭山崖墓建筑》。在《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中,陈明达解决了“卷杀”等疑难问题,受到梁思成的夸赞,称:“明达有奇思”。
1949年后,除了主持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古建筑保护的日常管理工作,陈明达还发表多篇论文,提出了他的古建筑保护思想。
1962年,陈明达率黄逖、彭士华再度考察应县木塔,并开始绘图与论著撰写,1966年《应县木塔》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在营造学社早年工作基础上更上层楼,通过精细的测量与缜密的分析,研究应县木塔的设计建造规律,对我国建筑史学研究影响巨大。同时期,陈明达先生还出版了《巩县石窟》,其研究视野除了古建筑还包括石窟寺的雕塑艺术……
在《陈明达全集》出版之际,20年来一直在整理陈明达学术遗产的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丁垚接受了澎湃新闻采访,谈及了陈明达的学术贡献。
澎湃新闻:从早期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实地测绘调查,到在文物局从事文物保护与管理体系的建设工作,再到之后的建筑史学研究及出版,陈明达一生与古建筑研究及文化遗产保护相伴。在您看来,陈明达是个怎么样的人?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倡出版《陈明达全集》,做一个全面梳理的?
丁垚:陈先生是一位深刻的学者,梁思成、刘敦桢先生都是他的老师,他和刘先生都是湖南人,而且家族在清代都有过显宦,经世济用传统很强。陈先生是大大拓展了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开辟的中国建筑史学,全方位继承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传统,开一代学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建筑的学人几乎没有人不受他的影响,他提出的学术问题不停被后学学习、论辩,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如果说他是继他的老师们而为上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恐怕也不为过。他的学术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而且在东亚建筑学界也有巨大影响,同时也包括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建筑研究者。
当然这些认识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过程,就是伴随着我从读研究生以来对陈先生著作的学习经历。我是1995年考进天津大学建筑学系(今建筑学院),世纪之交开始在王其亨老师指导下做毕业设计、读研究生。而之前的1980年代中,王老师读研时就是向陈先生学习《营造法式》,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渊源。当时陈先生并不在高校,但因为他研究深入、水平高,所以王老师是在前辈介绍下、自己找过去,有备而来地去跟随陈先生学习。陈先生也十分看重王老师的学术成绩,《全集》就收入了他在1984年7月给王老师硕士论文写的评审意见,评价极高,列出五大学术贡献,而且开头和结尾重申推荐用这篇硕士论文申请博士学位。所以陈先生向殷力欣嘱托身后事时就让他多请教王老师,这是天津大学师生学习整理陈先生学术遗产的缘由。二十多年前,我在跟王老师读研究生时,虽然论文方向不是《营造法式》,但王老师发现我对这方面感兴趣,读《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有些心得,也自己去跑了一些华北的古迹,他就开始安排我参与学习、整理一些陈明达先生的遗稿。当时殷力欣先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作为陈先生的亲属,殷先生在陈先生暮年时帮助他整理一部分文集,虽然只有文字,但也很重要,是我们后来的重要工作基础。2003年我留校工作,王老师又安排我教研究生的宋营造法式课,于是整理工作就更系统一些,更多研究生都开始参与。至于我提出编纂陈先生的全集要到2010年左右了,那时候是我们出了一本书,是陈先生的遗稿《营造法式辞解》,他生前已经誊写编次完毕,题目也是陈先生原拟,但生前未发表,我觉得对初学者很有好处,就花了几年的时间带同学们一起整理又补配了一些图。因为到这时候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年,对陈先生的著作文章也比较熟悉了,所以十几年前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跟殷力欣先生还有我们一起做工作的同学们聊起来,比照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全集的先例,完全可以有一部类似规模的陈先生全集。但当时拟的卷次跟现在的有些差别。
总的来说材料比较早就已经成熟了,但这么大规模的出版是不容易的事儿,在这个问题上,浙江出版集团挺有魄力,几年前,我把徐凤安、潘邦顺先生介绍给殷先生,很快出版计划就敲定并启动了。目前出版的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已是一个不容易的成果,学界也十分看重这件事,全国各学校的几位老师参加了编辑整理的工作,这次还有很多老师从外地专门来京参加周末的座谈会,都能看出来大家还是十分重视陈先生的学术遗产的。大家都是从自己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建筑史学习,就读陈先生的著作,所以陈先生的著作学术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把自己几十年的时光托付给的学术事业的共同象征吧。
澎湃新闻:陈明达与莫宗江跟随梁思成、刘敦桢测绘调查了大量古建筑与石窟寺,参与测绘古建筑百余座。据说,中国营造学社留存至今的大量图纸,很大一部分都出自于莫宗江与陈明达之手。可否谈一谈陈明达的测绘与制图?
丁垚:确实,关于这一点,陈先生、莫先生的经验,到今天也很少有人能相比,他们到建筑现场测绘调查的经验特别丰富。详细测绘、草测调查摄影的加在一起可以说难以计数,而且那时候营造学社的眼光是很高的,尤其是北平营造学社的几年,他们想跟时局赛跑赶紧把华北大地最重要的古建筑都以科学方法调查、研究并有所记录。他们两位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测绘过中国建筑最多的人,地域也广,类型多,图画得好。当时出去调查,刚开始有些图还是梁先生亲自画的,后来他们俩年轻、上手快,学习能力强,很快就承担起大部分的测绘工作,这样的训练太重要了,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后来陈先生做的研究深入,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因为测绘现场的细致发现会引出很多深入研究的问题和思路。
营造学社的团队工作效率极高,以易县清西陵一带的调查测绘为例,当时是刘敦桢先生带队、总括全局,莫先生主要负责拍照,陈先生主要负责测绘。他们几年学习很快步入正轨,后来营造学社迁至西南,他们俩在学术能力上也日渐成熟,可以独当一面了。
至于营造学社的图纸,其实包括很多类,不同工作阶段、不同用途,问题比较复杂。除了从测稿到仪器草图和成图以至由此重绘的做模型的图,再比如梁先生指导莫先生为《图像中国建筑史(ChineseArchitecture:APictorialHistory)》画的插图,底图就是综合了学社若干年的工作积累,但成图主要是莫先生的妙笔,当然梁、林是做了很多指导。但如果今天说道这些图纸本身,自然还是以梁思成、莫宗江合署为宜,而不是只突出梁先生而省略莫先生。陈先生的图和莫先生又不同,前面说陈先生1984年给我们王老师的清代陵寝研究的评语为什么那么高,是因为他50年前就跟随刘敦桢先生测绘清西陵,图都是他画的,他是国内建筑界清代陵寝肇始的知情人啊。应县木塔的图也有特点,是个longstory,就先按下不表了。这些图这次全集收录了不少。
澎湃新闻:关于石窟寺的研究,除了营造学社的考察外,解放之后,宿白等考古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您觉得营造学社的工作相较于考古学者的工作及成果有什么差别?
丁垚:中国营造学社对石窟、造像的调查研究直到今天还是十分珍贵的学术财富。陈先生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以他和莫先生的共同努力把这条学术脉络延续了下来,而且有新发现。除了莫高窟学社没能造访——但梁先生最早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的文章就是莫高窟壁画和唐代建筑的问题,而且1950年代初陈先生就撰写了国内学界最早对莫高窟分类分期的专论,据殷力欣先生介绍是因为之前几位先生去调查莫高窟的报告未整理出来,所以有陈先生重新调查和报告撰写——华北重要的北朝至唐代的石窟营造学社几乎都去调查、研究过,云冈、龙门、巩县、响堂山……这样看来陈先生后来对巩县石窟等北朝石窟的研究,实质上就是1930年代营造学社工作的延续。
其实何止石窟研究如此,《营造法式》研究难道不也是这样吗?而且西南地区大量的唐宋石窟造像也因为学社南迁而“偶然地”又成了他们的田野,不仅如此,佛光寺、独乐寺、华严寺、应县木塔、隆兴寺等古刹内唐辽宋明的佛教塑像,不也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吗?这样综合一起看,我们今天怎么能不特别看重营造学社对中国石窟和造像的研究呢?在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的带领下,他们是把石窟当成大型的雕塑艺术与建筑空间艺术来看待的,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出发点。
当然,石窟也是佛教艺术的宝库,也是佛教史、地方史乃至国史的重要史料。但作为大型艺术作品的石窟,可能是营造学社前辈首先的着眼点吧,这也是后来陈明达石窟造像研究的学术特点。其实,陈先生对巩县石窟的研究,和应县木塔、独乐寺的研究,在他那里都是一样的,从方法上就是这样,这一点我个人体会比较深。他的几篇文章,还有对石窟测绘图的严格要求,都能看出是来自老师的影响,甚至除了他和莫先生讨论的所得,还能从文中读出梁、刘、林等老师们的思路。所以2019年我在列“营造学社之道”的中国营造学社90周年纪念展览大纲时,就特别列出了这么一章,就是学社对中国石窟的研究,而陈先生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
澎湃新闻: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是陈明达之于中国建筑学术最突出的贡献。据说,经陈明达批注的《营造法式》就有多个版本,包括“丁本”“万有文库”的版本等。可否谈一谈此次全集中收录的《营造法式》。
丁垚:陈先生对《营造法式》的研究贡献,是以科学方法结合实物对该书所包含的中国古代“建筑学”的深入挖掘。至于说在《营造法式》版本校勘的贡献,在朱启钤全力打造的中国营造学社这一学术团队里,还是刘敦桢先生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也最有心得。而当时陈先生在营造学社正好任刘先生的助手,所以在这方面他也近水楼台,得以亲炙一线学者们的教诲。就在这段时间,他手抄了一部《营造法式》,也把老师们的校勘批注一并抄录,这个“童子功”对他后来的研究当然非常重要。全集收入的就是这套《营造法式》,当时他大概18、19岁吧。
《营造法式》刻本只有一些卷页留存,保存至今的全本都是清抄本。100多年前朱启钤在南京“偶然”发现并随即石印的就是曾为杭州丁氏收藏的抄本,也就是“丁本”,是各种清代抄本里在现代最早出版印行的一部,所以大家用的比较多,刘敦桢先生当年就是用这个本子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南书房新发现的清前期抄本即所谓“故宫本”比对校勘,陈先生手抄的也是此本。陈先生另外有一种工作用本,前两年影印出版了,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因为底本是陶湘主事帮朱启钤印的仿宋刊本“陶本”而缩小,所以也可称“小陶本”。陈先生1950年代以后大概主要就用这个本子,字清晰好看,开本小又好拿。上面有很多陈先生的批注,这就主要不是狭义版本意义上的校勘批注了,而是营造设计内容上的。这个本子后来陈先生送给我们王老师了,所以又成为王老师的工作用本,上面也有他的批注。前两年印行仓促,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个本子的由来特点等方面说清楚就出版了,现在看来很不合适,还得找机会补救。
澎湃新闻:《全集》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全”。可否谈一谈与过去的选集相比,这次补充了哪些内容?哪些内容是比较难收集和汇编的?
丁垚:我觉得有两点吧。一是过程史,二是个人史。它当然首先应该是陈先生著作文稿的汇集,但很重要的是,在殷力欣先生以及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收录了很多陈先生在他做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从他不到20岁在营造学社在老师指导下抄的书、画的图,直到他近80岁写的文字,种类则包括手稿、研究草图、表格、测稿、建筑摄影、绘画等,可以说是个全方位呈现。宋人就说:“古语云:‘大匠不示人以璞。’盖恐人见其斧凿痕迹。”陈先生这么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大艺术家”,我们今天把这些不同阶段的他的研究、工作甚至是成长的过程呈现出来,家底儿都抖出来,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没经过作者本人同意啊,而且也不可能了。但我个人以这20年从初学者到有了很多经验的学习者的学习体会看这件事,是希望它对更多初学者、年轻人有好处。我在别处写过这样一段话:“和他的老师梁思成、刘敦桢的《全集》一样,陈明达的《全集》所承载的,依然是一位中国的建筑学人从少年到耄年的生命历程、学术历程与心路历程。孔子说,如果你想选择一条道路作为人生的道路走下去,不踩着前人的足迹走那也是很难啊。《陈明达全集》呈现的,满是他和同学好友跟老师学习的足迹,我们翻着翻着书,就跟着走下去了。”
跟二十多年前的选集相比,这次最明显的就是多了很多图,当然也有点过度,这个还得在再版时重新把握一下。陈先生少时在营造学社接受的还是建筑师的教育,甚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国内最好的建筑教育,因为是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这些老师很多时候手把手地教。所以这个背景是跟着他一辈子,突出表现就是一直在画图,这也是我们这个建筑(architecture)专业的特点,尤其是巴黎美术学院传统的“esquisse”,我们自己说叫“草图”,但这种草图其实是整合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一种“科学图”,尤其是在考虑到种种现实条件和需求的同时、对比例(proportion)的推敲,图本身就是叠合了很多研究(study)的分析(analytique)过程。这种图是画起来很快,尤其对于构思(idea)阶段,都是创作、设计的思绪和思路。可以说我们学科的专业性都在这些图里头了,所以我们学这个专业的人看这些图是不一样的,会别有一种滋味。而我们的老师们,包括陈先生、莫先生他们的老师们,都是深谙此道,图画得特别好。全集在这方面收入了不少材料,包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对这事也很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大约20岁时候的测绘草图,很漂亮。
还有一类是生前录音的整理稿,其实讲话的效果不容易还原成文字,但很生动,很有些文稿体现不出来的传主形象。这主要是1980年代王老师派研究生采访陈先生录制的,讲他的学术经历、看法,十分珍贵。本来1990年代已经整理过一点儿,后来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王老师又找出来,正好我同学有朋友能帮忙转成mp3格式,就更方便了,在电脑播放用耳机天天听,都能背下来了。“音容笑貌”也有一半了,所以我虽然没有见过陈先生,但总觉得除了学术上的理解和认同,还有这些部分也很重要。包括他的颜体字,也很有个人特色,这个殷力欣先生也曾转述一些趣事,我想这些对于理解一位有过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又学习了新的建筑学术的学者,都是很重要的吧。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陈明达自己的学术特点是怎么样的?他是如何传承了老师的特点,又演变出自己的风格的?
丁垚:陈明达建筑学术的最大特点还是关心建筑设计,当然,这也是建筑学术的基本特点,否则还叫什么建筑学术呢?建筑学术,如果不谈设计、艺术和文化,那还能谈什么呢?即使先谈别的,也还是要引向这几方面,陈先生在他的著作里一再强调这是他从梁先生那儿学来的。当然,时代用语有时候用“构图”更多些,其实就是以图形媒介所做的整体形式把握,陈明达所做的关于木塔、北朝石窟以及独乐寺建筑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对于木构建筑,他觉得结构、构造、雕塑都要放到整体构图里看,对于石窟,他觉得造像、浮雕、装饰也要放在整体构图里看,同时再看单独的造型手法、结构施工问题。
陈先生的建筑学术还是受梁先生影响大,关心建筑设计、关心建筑和雕塑作品的整体、关心古代建筑的贯通性问题。如果排除掉时代性的差异,你会发现陈明达的研究和梁思成是很像的,跟刘敦桢比,他们更像一些。梁先生高明,陈先生深刻,从他们对独乐寺的研究就能看出来。刘先生也了不起,读书多,极渊博,他们都是不世出的学者,都是我们中国建筑学术的奠基人。
转自:澎湃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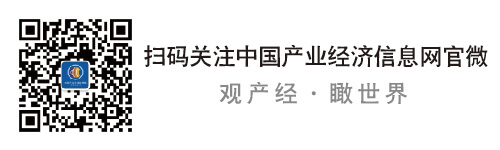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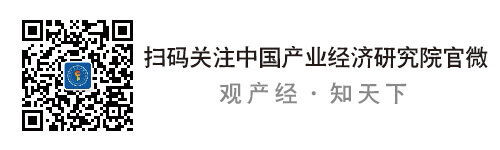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