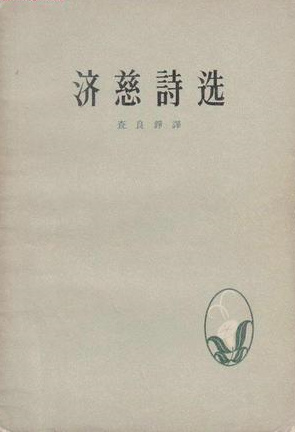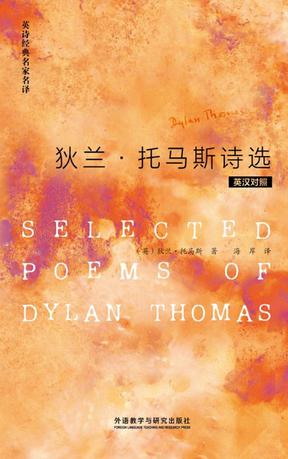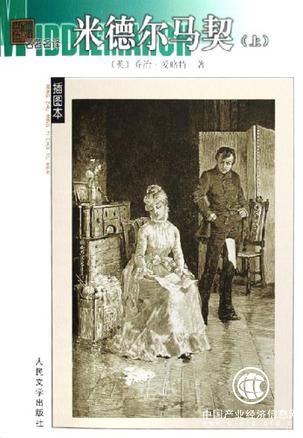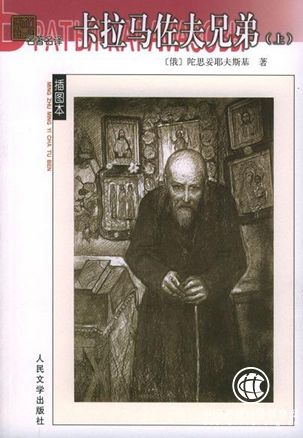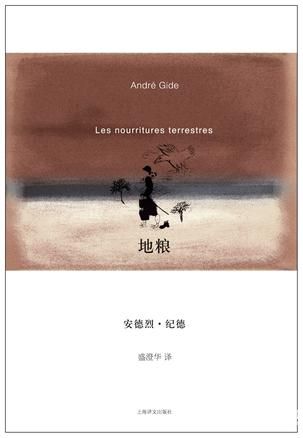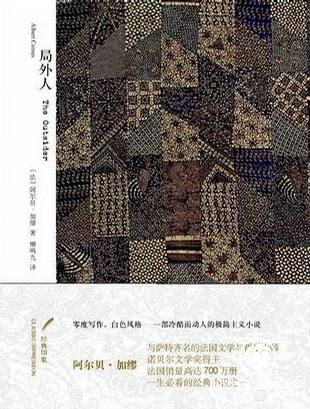反叛,大概是天蝎座作家的共同底色。他们就像弥尔顿笔下的撒旦一样,拥有源源不绝的“叛逆的激情”。哪怕这种叛逆已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他们也会死死钳住“命运的咽喉”,不作妥协。由于耻居人后,他们往往开一代新风,且绝不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而是决意成为无法超越、仅供膜拜的对象。天蝎座的作品,因此表现为智性的成熟和意志力的强韧,而缺少温柔的部分,即便女作家乔治·艾略特,也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闷骚”的他们由于心机深,故而作品编制得颇为烧脑。阅读天蝎座的作品,第一需要胆量,不被其天生的反骨所惊骇;第二考验智力,否则你会觉得文字背后有一双满是嘲讽的眼光打量着你,仿佛在说:“哼哼,读懂了没?”
济慈(1795年10月31日)
《济慈诗选》
五四时代,“摩罗诗人”拜伦吸引了许多文学革命者粉丝,而雪莱则是青年男女膜拜的对象,相比之下,济慈由于过于纯粹,而未曾获得过如此疯狂的追捧。然而在三位浪漫主义诗人中,济慈No.1的地位却是最为稳固的。相比拜伦、雪莱置身其中的激情,济慈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激情,他认为,诗人应像莎士比亚那样有能力排除内外世界各种干扰:“一名诗人是生活中最没有诗意的,因为他没有自我——他要不断地发出信息,去填充其他的实体。太阳,月亮,大海,世上的男男女女,作为一种有冲动的生灵,他们都是有诗意的,因此都有不变的特征——而诗人却没有,没有自我。”我想这就是天蝎座的济慈如此让人捉摸不定又回味无穷的原因吧。
《济慈诗选》,[英]约翰·济慈著,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狄兰·托马斯(1914年10月27日)
《狄兰·托马斯诗选》
每一个天蝎座都是疯狂的,自毁的,但疯狂的形式个个不同。“疯狂的狄兰”是20世纪英语世界绝对名列前茅的诗人,他那点石成金的语言魔力,吸引了无数粉丝,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歌手鲍勃·迪伦,《星际穿越》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济慈出身贫寒,狄兰没上过大学,他们那种自傲糅杂着自卑的心理,使得他们行为乖张,言语癫狂。有一次狄兰与卓别林和玛丽莲?梦露共进晚餐,而他在饭前就喝醉了,卓别林很生气地把狄兰赶走,说伟大诗歌不能成为发酒疯的借口,狄兰的答复是在卓别林家门廊的一棵植物前撒了泡尿。39岁时他因连喝了18杯威士忌而暴毙,然而伟大诗歌让更多读者愿意选择忽略他的疯狂,聆听他的高贵,像《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中的诗句,已经脍炙人口,正如诗人所说,他“唯一的高贵的心在所有爱情的国土上都有见证人”。
《狄兰·托马斯诗选》,[英]狄兰·托马斯著,海岸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乔治·艾略特(1819年11月22日)
《米德尔马契》
这个名字恐怕有些人都没听说过,大家只知道T.S.艾略特。在英国小说史上,她的名字是和简·奥斯丁、狄更斯放在同一行列的。在著名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眼中,乔治·艾略特简直就是英国小说界的女神雅典娜,足以与泰坦巨人托尔斯泰相媲美。而作者本人的传奇人生,恐怕比其作品更加惹眼。她是个虔诚信徒,后来却放弃基督教;她是个女小说家,却撰文抨击“女小说家们写的蠢小说”;她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是“温柔敦厚”坚持清教徒式生活准则的时期,然而她却与有妇之夫过起了非法同居生活,离经叛道;她将近四十岁才开始小说创作,却成了首屈一指的小说家,相信足以作为当代妇女借鉴的楷模。
《米德尔马契》,[英]乔治·艾略特著,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屠格涅夫(1818年11月9日)
《猎人笔记》
天蝎座当然是叛逆的。优美的屠格涅夫也不例外。你只要想想那群捧着伏特加叉着熏肠醉醺醺的俄国人,就能明白“洁癖症患者”屠格涅夫是多么叛逆,他恐怕是俄国作家中最不像俄国作家的俄国作家了。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但其在短篇小说领域的成绩,恐怕要大于长篇的成就。
《猎人笔记》是其巅峰之作,它是如此轻盈、鲜活、纯净而完美,没有夸张的修辞,没有浮躁的情绪,不含一丝粗俗的气息。这是一种文学教养,更是作者把文学提纯的天赋。屠格涅夫式的净化,就像西方油画中的小天使,他们裸露的性器官都能给人可爱的感觉而不让人产生情欲的联想。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土地难以言喻地一尘不染,如雨后的“白净草原”,你简直可以嗅出故事里空气的味道,不用细辨,一定是甜美的。
《猎人笔记》,[俄]屠格涅夫著,丰子恺译,译林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
《卡拉马佐夫兄弟》
托尔斯泰把传统的文学技艺发挥到极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托尔斯泰代表着俄罗斯受到西方影响的高级阶层的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体现了俄罗斯社会乡野的灵魂,他是如此的桀傲不驯,如此的奇妙无比,致使尼采读了他的《地下室手记》后欣喜若狂,赞之为“一段真正的音乐,一段非常奇异的,非日耳曼的音乐”。托尔斯泰是平和温暖的,即便是絮絮叨叨的说教也是和蔼可亲的;而陀氏一生都在弹奏令人颤栗的不和谐的声音。他怀疑一切为世人认可的规则,他怀疑常识、科学、理性,怀疑“二二得四”这样一种似乎毋庸置疑的圭臬。就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许多哲学青年顶礼膜拜的当代“圣经”,《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了考验文学青年的“试金石”——首先,你得有这个耐心读完。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安德列·别雷(1880年10月26日)
《彼得堡》
在眼高于顶的纳博科夫心中,安德列·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变形记》相提并论的20世纪西方四大名著。1916年《彼得堡》问世,标志着现代主义小说在俄罗斯率先横空出世。当其时也,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的代表作都还在写作过程中,别雷可谓先声夺人。然而别雷对语言实验的迷恋就像乔伊斯一样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读者只好纷纷表示“看不懂”。作者说,这部小说“实质上是对被意识割断了同它自然本性联系的瞬间下意识生活的记录。不妨把这部长篇小说称作是‘大脑的游戏’”。“大脑的游戏”这一概括,非常精准地指出了这部“侦探”小说的烧脑属性。
《彼得堡》,[俄]安德列·别雷著,勒戈、杨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纪德(1869年11月22日)
《地粮》
木心曾说,尼采是威士忌,纪德是葡萄酒,可见都是能醉人的。只是一个烈性酒,一个后劲大。骨子里都是反叛,尼采是蓬头垢面的纪德,纪德是优雅克制的尼采,尼采是“狂人”,纪德是“闷骚”。的确,对比尼采的义无反顾,纪德的内心充满了灵与肉、禁欲与享乐、信仰与怀疑、赎罪与反叛、恪守道德与蔑视戒律的矛盾杂糅。《地粮》是纪德以抒情的语言,糅合传统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一连串富有诗意的随想录。他以爱与热忱化作颂歌,凝成字句,被奉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我乐意地责笞我的肉体,在惩戒中比在过失中感到更大的喜悦——我曾那样地陶醉在不仅为罪恶而罪恶的自傲中。”读到这样“SM”的字句,还真让人心里有那么点不安呢。
《地粮》,[法]安德烈·纪德著,盛澄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加缪(1913年11月7日)
《局外人》
加缪把他的一本哲学随笔集命名为《反抗者》,经由对西绪弗斯神话故事的天才阐释,他将卡夫卡对命运的洞见变成一种以接受命运为前提的对命运的反抗。默尔索这个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局外人”,面对母亲的死亡,他拒绝悲伤;面对法律的审判,他拒绝认同;面对装模作样的牧师,他拒绝忏悔。他不仅拒绝尘世,也拒绝天国。他以彻底的陌生人形象面对人们熟知的世界,用不近人情作为反抗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局外人”因此成为了“叛逆期”青年的代言人,一度火爆到“开谈不说《局外人》,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程度。
《局外人》,[法]阿尔贝·加缪著,柳鸣九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穆齐尔(1880年11月6日)
《没有个性的人》
安德列·别雷的《彼得堡》,翁贝托·埃科的《玫瑰的名字》,无论显得多么“学霸”,毕竟还披了一件推理小说的外衣,制造那么一个“暗杀事件”或“连环杀人事件”的迷宫吸引读者看下去,但穆齐尔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他根本不关心读者能否读得下去,他那近百万字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几乎没有故事情节,充斥着作者对人类历史、哲学、科学、文学、艺术、道德、法律、心灵、理性、激情、欲望等等的思考与见解。令人怀疑他是不是把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改头换面地拿出来发表了。一位德国文学批评家曾说过:“毋庸讳言,《没有个性的人》好比一座沙漠,沙漠中虽有几处景色优美的绿洲,但是从一处绿洲到下一处绿洲的跋涉往往令人痛苦不堪。没有受虐心理准备的人还是趁早投降为好。”
《没有个性的人》,[奥地利]罗伯特·穆齐尔著,张荣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萨拉马戈(1922年11月16日)
《失明症漫记》
那位写出了《修道院纪事》《失明症漫记》等神奇作品的“极富想象力”的葡萄牙小说家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为什么是愤怒?因为萨拉马戈悲天悯人地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正如一份讣闻所言:“他反对过军政府,反对独裁,反对教会,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反对布什和布莱尔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反对任何政府对任何文学作品的任何审查,反对伪善的和吃人的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化……”反叛的他简直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用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讽所维系的关于这个世界不甚友好的寓言,却“让我们把握到捉摸不定的现实”。(卜雨)
《失明症漫记》,[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南海出版公司
转自:澎湃新闻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