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章学”发微
——《文心雕龙》的架构与学理
作者:赵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
编者按
近百年来,学界基本是以西学的眼光来剪裁和评骘中国古代文学的。其结果,不是造成削足适履的难堪,便是留下隔靴搔痒的遗憾,甚至弄出买椟还珠的笑话。鲁迅先生在《叶紫作〈丰收〉序》中感叹道:“《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不仅小说如此,诗歌、戏曲同样如此,文章尤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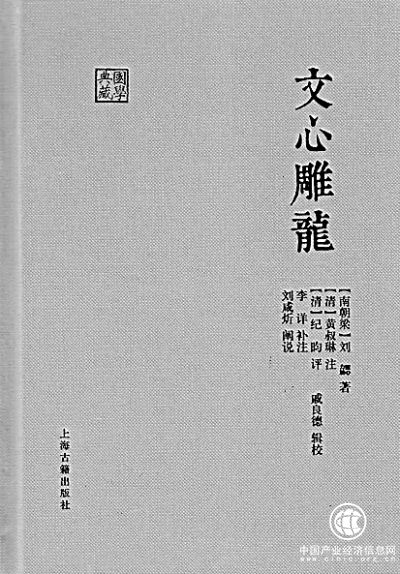
《文心雕龙》 资料图片
中国古代许多文章根本装不进西方“散文”这个筐子,中国许多古代文章家的艺术感觉极为细腻,神、韵、理、气、涩、峭、趣等审美范畴,又大多在西方散文理论视野之外,用西方的散文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文章,不出现方枘圆凿那才是奇迹。汲取中国古代文章学智慧,重构中国当代文章学,以中国话语谈论中国文章,是当今中国学人应有的学术担当。
这里的三篇文章皆阐述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三位作者皆是这一领域的学术名家或学术新秀。赵昌平先生从《文心雕龙》的构架和学理入手,论析中古文章学的理论体系,要言不烦又切中肯綮。此处“文章学”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此处的“文章”兼容六朝的“文”“笔”。熊礼汇先生精细地辨析了三个关键词的内涵与外延,此文的“文章学”则属于狭义。余祖坤先生论及古代骈、散和八股文评点的价值与开发,而恰如我们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历史古迹一样,学界至今仍旧冷落了祖传的文章评点。(戴建业)
中古文章学,是以文章为研究本位的文学理论体系。其发生、发展经历了由汉魏以迄中唐约600年,而《文心雕龙》则集前代之大成,开唐人之法门,堪为其典范之作。本文拟由是书之总体架构与学理着手,阐明“文章学”并无待当世学者去重新建构,而是早在一千五六百年前业已完成了具有语言批评性质的、体大思深的民族性文学理论体系。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情采》),可见以“文章学”指称刘彦和的体系是合其本意的。一般认为是书上篇二十五篇为文体论,下篇二十五篇为创作论,却鲜有对其上下篇及各子篇相互关系的论析。值得注意的是后序性质的《序志》对全书架构的提示。
《序志》称上篇为“纲领”,下篇为“毛目”。纲举目张,可知下篇所论创作思维与为文“要术”(文要、文术)一系于上篇所论以《原道》《征圣》《宗经》为渊薮,以《正纬》《辨骚》为正变枢纽的二十二类文体之流变。这与挚虞《文章流别集》及《序》、昭明《文选》之文体分类,表现出一致的时代倾向。由此,一个初步的判断是:此书是一种合文体流别史与文章学原理于一体的大著作,而绝不只是“写作指南”之属。最能说明这一性质的是与《原道》等三篇遥应的《时序》《物色》二篇的性质与位置。所谓“创作论”,其实止于下篇自《神思》至《总术》一十九篇。《时序》领《物色》,紧接其后,是关合下篇创作论与上篇文体流别论的“接榫”。这可由创作论十九篇各自的理论要点及内在联系悟得。
《神思》居下篇之首,为创作总论,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神与物游”的思维特征,更重要的是以“神思”——心神之作用为关键,发展了传统文论“言、象、意”关系这一核心命题。所谓“心总要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说的是心居主位将引发创作冲动的心、物之主客对待,转化为主体内在的志气与辞令的虚实互摄。这一点成为贯穿创作论以下各篇的红线,故是篇总结“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谓:在积学、酌理、研阅、驯致基础上,“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学创作的实质就是心体这位大匠,以其玄解、独照的功夫,妙用兼具声象的言辞以呈象达意的“密则无间”之过程。《神思》赞云“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正是对以上理路的概括。
心为主体虽同,但文章风格各异,故以《体性》置《神思》后加以阐发,其最重要的理论创获是对庄子“成心”概念的改造。彦和所谓“成心”,是指区别于人人皆有的“心”体(共相),而因人以异的性情化的性心(异相),它由各人先天的禀赋“才”(智质)、“气”(气质)与后天的“学”(文化传承)、“习”(时风熏陶)结合而成;文章虽风格有别(八体),而究其实,无非是“各师成心(性),其异如面”。这就将普遍性的“神思”,提升至个性化创作的境地,是对传统的“言为心声”说的重大发展。《序志》以“摛神性”来提挈二篇关系,其中实包含了彦和新论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支点:个性化与对语言形式的重视。
八体有殊,然其通则是“会通合数,得其环中”,以下《风骨》篇即论此义。“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可见风骨固以“务盈守气”为本,然而气又必待端直准确的言语方能得到骏爽的抒发。“风清”与“骨峻”上承“意”与“辞”关系而深化之,同样是虚实互摄的一个问题之两个方面。
风格之体又必须附丽于一定的文体方能呈现,故复次之以《通变》《定势》,将风格之体关合于文体之体,从而由创作主体的维度,打通了创作思维(目)与文体流变(纲)的关系。“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因此能文者虽或“总群势,通奇正”,“随时而适用”,但“镕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所以作者的每一次创作,一方面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另一方面则在“循体以成势”的同时“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即主于成心的即时作用“随变而立功”。故《定势》赞以“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来概括之;而《序志》在“摛神性”后,继云“图风势,苞会通”,更提挈了以上各篇关系。
特定的“情采”自凝于某一文体,即生成具体文章(今称文本),以下《情采》《熔裁》即承上申论这一“括情理,矫揉文采”的过程,而其“蹊要所司,职在熔裁”。“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谓之裁。”此本体,注家多谓指思想内容,然上文云“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可知本指情理(情之理路),体指文体。虽云“因情立体”,但本与体未必丝丝入扣,故须“变通以趋时”,通于传统而变于当时,且由成心之妙用“熔”情入“范”(文体),按部就班,是为“情理设位”。这一过程同样是通过“文采行于其中”并加以剪裁呈现的。由此彦和将传统的“言志”说,提升为“情经辞纬”说,去纬无以言经,故在反对“为文造情”的同时,充分强调“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可见文本之情理与辞彩的关系是意辞互摄的创作活动的最终体现。
以上自《神思》至《熔裁》七篇即“心总要术”之要(文要),术系于要,故《熔裁》又下启《声律》至《指瑕》九篇,以“望今制奇”而“参古定法”为要旨,论各种文术之运用务必得中合度而体要,是即《序志》所谓“阅声字”;更以《养气》《附会》《总术》三篇总束之以呼应论文要七篇。如此总而分,分而合,系统地阐释了文学创作以成心为主体,将心物对待的创作冲动(直觉)转化为个性化的意辞互摄以呈象见意的语言活动,并终于产生“三十辐共一毂”、情采彪炳的文本这一内在理路。这一文本因此似“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而苞情含风的语言组织,这不能不令人想起英国人贝尔关于作品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的命题。20世纪中叶,境内学界受苏联清算形式主义的影响,普遍以“形式主义”贬称六朝文学,可称是“歪打正着”。
然而彦和心目中意辞互摄的文章,虽具有相对的自足性,却更在两个维度上具有开放性,从而体现出中古文章学语言形式批评的民族性格。《序志》将作者“割情析采,笼圈条贯”的功夫归纳为“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后,即接云“崇替于《时序》”,而《时序》领《物色》,二篇正居创作论十九篇后。这样就呼应上篇,将作者以成心为主体的语言活动置于纵向的文体(文风落实于文体)崇替与横向的时代风会之交汇点上(《物色》下《才略》《知音》《程器》三篇为有感而发的余论,性质近乎批评论,此不赘)。《时序》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的是文章十代九变,因于世情之变化(时变)而呈现为一种演进序列,而《物色》更进一步发明作者“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之特定情境下的个性化创作,正是“文变”“崇替”的原动力。所谓“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意有余者,晓会通也”,揭明了一种事实:无论自觉与否,主于成心的作者的创作活动,都是对文体的因乎时、染乎世的承中有革,这是彦和文学史观的核心。而参以《体性》所说“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观之,就认识论而言,实与当代发生认识论暗合。作者童年时的习学会影响其最初的创作倾向(认识图式),它一方面对其一生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因其处于传统与时风的交汇点上,而在情境化的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会通古今,异代接武,参伍因革的文学之世变,自然也积渐地改变着原初的创作倾向。这种观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作家文风演变的着眼点,更为解答学术界聚讼既久的“外部因素如何转化为文本内涵”问题提供了答案。这种转化的中介,就是“成心”。作者通过学、习,将诸多外部因素(可总称为一时之文化)融入其先天禀赋的才(智质)、气(气质),使之化为成心的有机成分——已被才气个性化的有机成分,是为前创作阶段的潜识与潜能;一旦物我相击,某种潜识被外物唤醒,潜能则通过意辞互摄,个性化情境化的语言活动做成文章:这样外部文化诸因素便自然转化为作品个性化的内涵了。
以上无论是“语言形式批评”“发生认识论”,都用了“暗合”一词,这是说研读《文心雕龙》可以二者为参照,而彦和以上新论的切实的学理背景是对传统学术的“通变”。兼为儒家五经、道家三玄之首的《易》学,是汉魏以降的显学,而王弼注《易》,更开启了《易》学由重象数向重义理的转化。笔者认为以《系辞传》为代表的易学的思辨形态可以用这样一组范畴来概括:中(道)——时——势——经权与通变。人对于不可言喻的中道的把握,其实是因时审势而得其度,从而执经用权,通于古而变于今,是为通变。《文心雕龙》通贯全书的“望今制奇”而“参古定法”红线,无疑是《易传》思维形态的文学表现。
与此相应,魏晋以降,何晏崇本举末说代替“崇本黜末”说成为本体论的主流认识,而郭象驭物得中合度而不过当即为顺物之天性说,葛洪学习有以砥砺人的天性说等等,则又对《易传》人可参与天地造化及道与术数之关系的思想作出了重大发挥,从而在以上思维形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然观:万物分殊理一,所谓顺应自然,并非绝圣去知,而是各具成心的具体的人的心之理与具体的物之理的密合无际。《神思》篇以“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冠于心匠意辞互摄的创作语言活动之前,正是以上时代性儒道互补的新思维的反映。而当时各文化部类的细分化研究,尤其是文字学、音韵学、文体学的长足发展,更为以上新自然观率先在文学领域催生《文心雕龙》这样划时代的理论著作作出了铺垫。
至此可悟,被视为全书总纲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并不能说明彦和一禀儒家立场。细读文本,三篇并非对儒家教义的阐发,而只是视六经为二十二类文体之渊源,并标示一种雅丽的语言传统,作为“望今制奇”而“参古定法”之典范,三篇下接《正纬》《辨骚》为文章枢纽,正可见以上理路。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21日 13版)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

版权所有: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京ICP备11041399号-2京公网安备11010502003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