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在工业化食品和不成熟营养学的推波助澜下,人类创造了新的食物链。餐桌上的食物与它的源头越来越远,而人类则萎缩在工业化食物链的末端,丧失了与自然之间的原始记忆。传统科学认知的转变带来一种日益流行的饮食焦虑,到底该吃什么,吃多少,按照怎样的程序吃,用什么来吃,什么时间吃,以及和谁一起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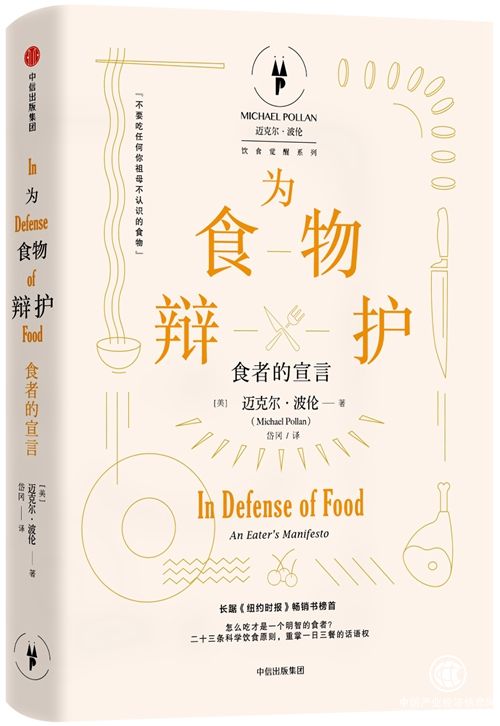
《为食物辩护:食者的宣言》,[美]迈克尔·波伦(MichaelPollan)著,岱冈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5月。
美国饮食作家迈克尔·波伦长期关注饮食问题的方方面面,企图在工业社会与田园自然中寻求调和。本文摘自其《为食物辩护:食者的宣言》一书,原题为《被牺牲的饮食之乐》,波伦认为吃的理由绝不仅仅是吃本身,食物还关乎快感,关乎人际交往,关乎家庭和精神生活,而营养哲学,“姑且不论能否为我们的健康做些什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它夺走了我们享用美食的大部分快乐。”本文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我们食者,从营养主义那儿得到的好处可没有食品生产商得到的那么多。除了向最新批准的貌似食物的物质发放许可证以鼓励人们多食(对此我们十分赞同)之外,营养主义着意要培养人们亲身体验购买食品和享用食品的巨大热忱。为了吃得正确,你必须与最新的科研成果保持同步,还要研究越来越长且让人发晕的食品成分标识、仔细审阅益发令人怀疑的健康声明,然后才可以享用你想吃的食品,不过这些食品可都是按照某些预期的目的进行过设计,而绝非仅仅追求味道好。将食品中最美味的成分想象成毒素,一如营养主义教我们如此想象脂肪那样,是不会给我们作为食者的幸福感带来什么的。美国人业已信奉这门“营养哲学”,借用简·布罗迪的话来说,姑且不论此哲学能否为我们的健康做些什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它夺走了我们享用美食的大部分快乐。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一定需要这门营养哲学呢?或许,这是因为我们美国人从来就很难从吃东西中获得快感。我们肯定是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来避开它。莱文斯坦曾写过两本插图本美国食物文化史,他指出,美国食物的极端丰盛养育了“一种似有似无的对食物无所谓的态度,突出表现就是美国人都喜欢快吃即走,而不是细嚼慢品”。品鉴美食或将大快朵颐当成一次美学体验,这都被视为明显的腐朽没落,以及海外纨绔之风的一种形式。除了享受美味佳肴之外,还真没有什么能把美国的政治候选人扳倒的,这个现象是马丁·范布伦(MartinVanBuren)在他1840年竞选连任失败时发现的。当时范布伦将一位法国大厨引进白宫,铸成了大错,遂被其竞争对手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HenryHarrison)紧紧揪住不放,而同时哈里森还利用自己“仅以鲜牛肉和盐就能过活”的事实大做文章。小布什对猪肉皮的喜好和克林顿对麦当劳“巨无霸”的情有独钟,都是政治上狡黠的个人口味秀。
正如莱文斯坦指出的那样,或许事情就是如此,在美国,食物的极端丰富的确培育出了一种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饮食文化。但我们作为清教徒的本真也阻碍我们从美食中得到感官的抑或唯美的享受。犹如性欲,食欲也将我们与动物联系起来,而在历史上,新教徒们的很大一部分能量都被用在了严格控制我们动物般的胃口上。在19世纪的基督教社会改革家看来,“吃作为一种赤裸裸的行为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而且除非具备非凡的判断力,一般也不被人视为一种快感”。此言引述自劳拉·夏皮罗(LauraShapiro)所著的《完美的沙拉》(PerfectionSalad),该书回顾了这些国内改革家们为使美国人信服所付出的努力,并借用其中一位的话来说,“食并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放任,而烹饪的目的也远比满足食欲和口福要高尚得多”。那么这个高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便是营养丰富和卫生健康。夏皮罗写道,通过抬高那些科学原则,并“贬低口舌之感”,“他们终于使得美国式烹饪在其后的年代接受了一大批破坏性的创新”,低脂肪加工食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因此,在饮食上讲究科学在美国是一个由来已久且受到尊重的传统。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塑造了美国人对待食物的态度的那些伪科学信仰,莱文斯坦这样总结道:“味觉并非引导人去吃应当吃的食物的真正向导;人不应当仅仅吃他喜欢吃的食物;食物中重要的成分既无法看到也无法品尝,只有在科学实验室里才辨认得出;实验科学产生了营养学的各种定律,用以预防疾病和延年益寿。”莱文斯坦在这里所描述的也许正是营养主义的主要信条。
伪科学饮食(以及原初营养主义)之最为恶名昭彰的泛滥也许始于20世纪初,当时约翰·哈威·凯洛格和豪瑞斯·弗莱彻说服成千上万名美国人以从饮食中所获得的一切乐趣来换取促进健康的食物疗法,而这些食物疗法的要求都是惊人的严格和反常。上述两位饮食大师在鄙视动物蛋白方面完全一致,坚信食用动物蛋白不仅助长人们自淫,而且还促使有毒细菌在人的结肠中大量繁殖。在美国食物盲从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蛋白质扮演的角色与脂肪在下一个黄金时代所扮演的完全一样。在凯洛格创办的巴特尔克里克(BattleCreek)疗养院,病人们(包括老洛克菲勒和西奥多·罗斯福)花上不多的费用,就能根据各自情况进行一些“科学”训练,诸如间隔数小时进行一次酸奶灌肠(以抵消蛋白质可能在结肠壁上留下的损害);做电刺激和肚子的“大颤动”;饮食只有葡萄(每日吃10到14磅);而且每餐吃饭,都要“弗莱彻主义”(主张细嚼慢咽)一番,也即每咬下一口食物,都要嚼上近百遍。(经常还配以令人亢奋的专为咀嚼而写的歌曲。)其中的理论就是,彻底的咀嚼将减少蛋白质的摄入(这一点似乎很确定),因此也就改善了“主观和客观的健康状况”。豪瑞斯·弗莱彻(也即“伟大的咀嚼者”),虽然没有人给他颁授什么科学国书之类的称号,但他本人超凡的健康状况本身就是最好的范例——他50岁时还能一口气在华盛顿纪念堂的898级台阶上快速跑个来回,中途并不需要停下来喘息,而平时他每天坚持只细嚼慢咽45克蛋白质的食物疗法,所有这一切就是他的追随者们所需要的证明。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兄弟俩双双成为热情有加的“细嚼者。”且不论上述饮食方法的生物学效应有多大,至少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将饮食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将饮食与口福之乐割裂开来;强迫咀嚼(间以小时计的短时灌肠)对于餐桌上的乐趣而言毫无益处。更有甚者,早在上下颚关合数到100下之前,细嚼慢咽就已令食物那最后一丁点儿香味消耗殆尽。凯洛格本人毫不讳言对饮食之快感的敌视:“贪恋美食盛行之时,便是民族陷于沉沦之日。”
若果如所言,美国便可高枕无忧了。
美国早期曾引入各种科学的饮食方法,或许这多少也反映出美国对其他民族饮食之道的反感:特别是外来移民那些稀奇古怪、乱七八糟、臭气熏天,而且还总爱什么东西都一锅烩的饮食方式。一个民族的饮食之道是表达和保存其文化身份最有力的方式之一,而这正是一个致力于“美国化”理想的社会所不需要的。使饮食选择更加科学化,其实就是掏空其种族内涵和历史;至少在理论上,针对像美国人那样餐饮的意义何在的问题,营养主义给出了一个中立、现代,而且将来还有望统一的答案。这一招将对外族饮食选择的驯化不露声色地化于无形。在这方面,营养主义很像美国人在家门口都要留草坪的惯常做法,因为这个做法没人会反对,哪怕有点儿冷漠,也还是可以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使我们的风光更加美国化。当然,在这两个例子中,达到整齐划一的代价便是失去美的多样性和感官上的愉悦。这也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转自:澎湃新闻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

版权所有: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京ICP备11041399号-2京公网安备11010502003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