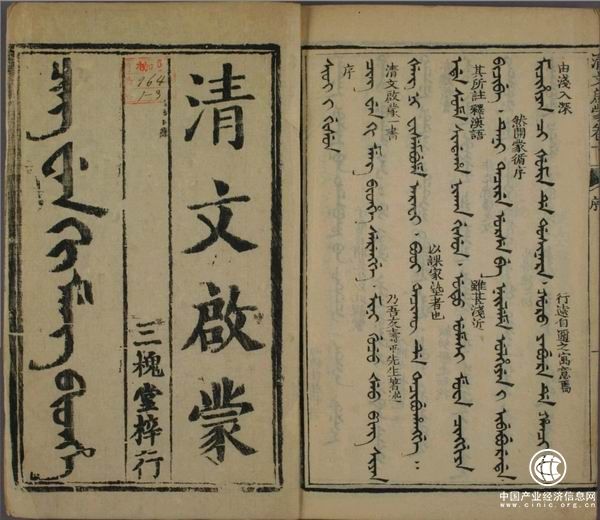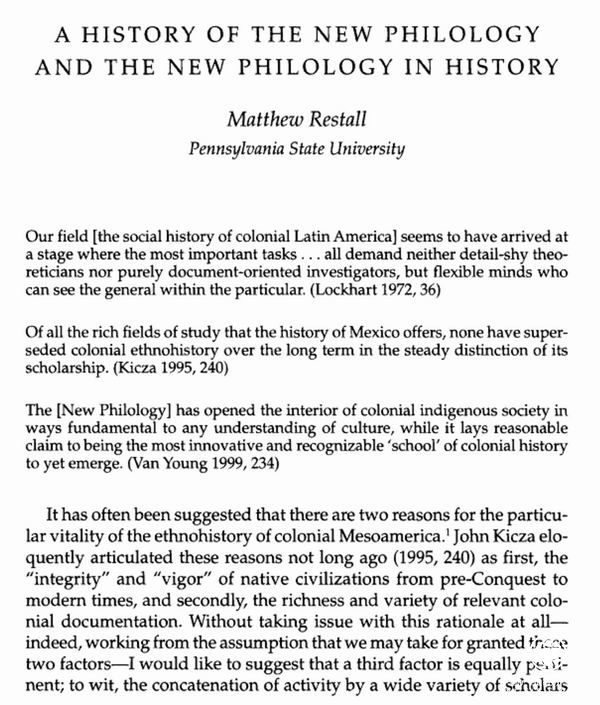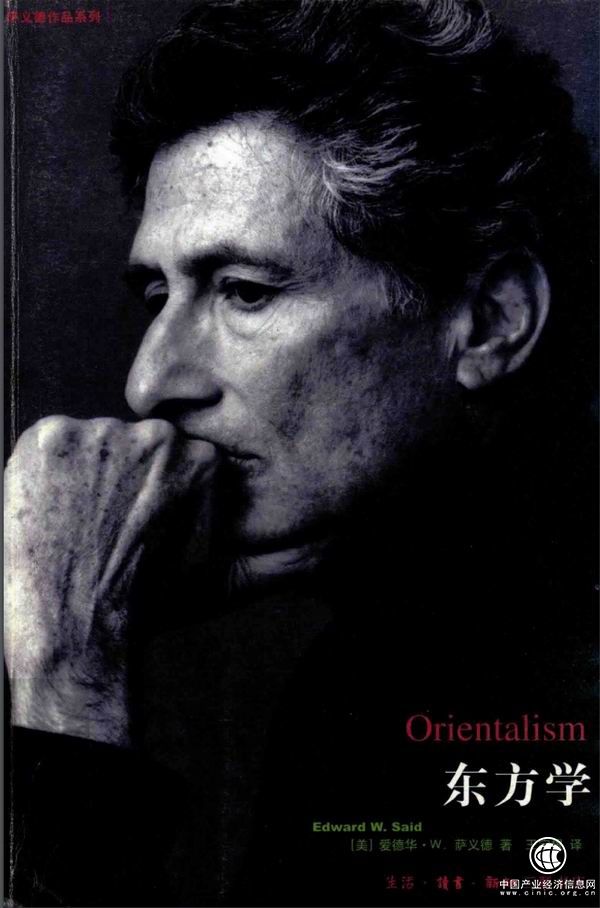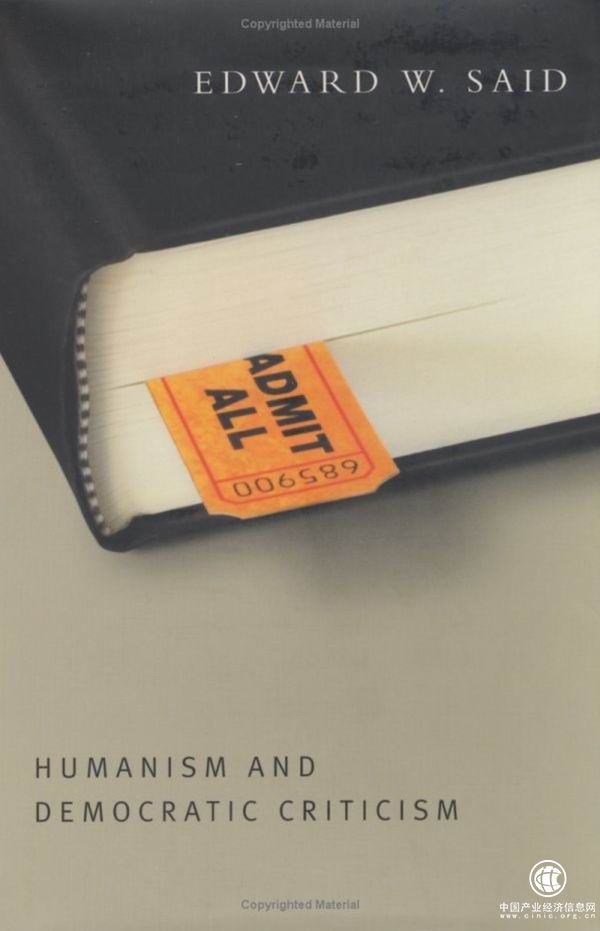【作者按】
本文的写作缘起于2016年10月22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持召开的“思想与方法——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时所作的一个简短发言,以后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陆续增补、写成。本文纸质版将揭载于由该学术论坛主持人方维规教授主编的学术论文集《思想与方法:历史中国的秩序变动与文明交错》(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中,于此作者衷心感谢方教授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并再三敦促我写成了这篇文章。
满文教科书《清文启蒙》
“新清史”的另一个学术主张,即清史研究应该重视利用非汉文文献,特别是满文文献,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识,毋庸置疑。大清帝国是满族建立的王朝,从其立国到灭亡,满族贵族、精英一直是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主导力量,满文是在清官方和民间始终流通和使用着的活的文字,迄今留存的满文文献资料极其丰富,它们自然和汉文文献一样,是研究清朝三百余年历史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不仅如此,正如“新清史”所强调的那样,清朝不但是一个“基于中国的帝国”,而且还是一个“内亚帝国”,所以要研究清史不仅要利用汉文和满文资料,而且至少还必须利用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等文献资料,清史研究的进步和发展有赖于多语种民族文字文献资料的发现、利用和比较研究。
可是,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清史研究和满学研究,或者说对清朝那个“基于中国的帝国”,以及那个“内亚帝国”的研究,长期以来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和学术领域。前者属于汉学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中亚学、内亚史或民族学、民族史的研究范围,所以,传统从事清史研究的人多半是利用汉文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汉学家,而从事满文、蒙古文文献研究的清代内亚史的人,则多半是中亚语文学家或内亚学者。譬如,哈佛大学中国研究的奠基者费正清先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位清史学者,他只利用汉文文献来研究清后期的历史,而他在哈佛的年轻同事Joseph Francis Fletcher先生则主要利用满文、蒙文、伊斯兰语文文献来研究清代内亚的历史,他的身份是一位中亚语文学、中亚历史教授。这样的传统在美国学术界长期保持着,如欧立德教授的老师James Bosson教授毕生从事满文、蒙文和藏文文献研究,他一度曾经代理Fletcher教授在哈佛留下的中亚语文学教授席位;与欧立德先生平辈的学者中有Johan Elveskog教授利用蒙古文、满文和伊斯兰语文文献研究清代内亚史,成果卓著,但他一般不会被人当作是清史学者,而更多被认为是一位中亚语文学家或者宗教学者。
精通满、蒙、伊斯兰文的中亚语文学家、内亚学家Joseph Francis Fletcher
如前文所述,“新清史”强调清史研究要注意其“内亚维度”,即要把对清“内亚帝国”的研究作为清史研究的重头戏,这意味着要把原来分属于两个不同学科和学术领域的清史研究整合到一起。这样的学术整合或与北美中国研究这个学科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有直接的联系。形象地说,正如今天的欧立德教授一人肩负的是当年费正清和Fletcher两位先生的教职一样,清史研究与内亚史、中亚语文学至少在哈佛大学已经合二而一了。在这样的整合中,中亚语文学和内亚学的“语文学”特征渐渐变弱,正在失去其过去曾经享有的十分崇高的学术地位,而对一个内亚帝国,或者说一个跨越欧亚的清帝国历史的研究,则不但超越了传统中国研究的范畴,而且还与近年来势迅猛的全球史研究的大趋势一拍即合,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整合中,以满文为主的非汉文文献资料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清史”学者对满文文献的重视,从其学术趋向和取径来看,或与同时代美国学界出现的所谓“新语文学”(New Philology)运动有一定的联系。当时有一批从事中美洲人种史、民族史的年轻学者,尝试以坚守“新语文学”来复兴他们的研究领域。而所谓“新语文学”,即强调土著语文资料的重要性,并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两种学术进路来处理这些土著语文文献。参见Matthew Restall, “A History of the New Philology and the New Philology in History,”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8, no. I, 2003, pp. 113-134.)
“新语文学”运动
随着“新清史”在国内学界之影响的不断扩大,它的所有主张都受到了严重质疑和挑战。围绕满文文献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与其说是一场学术的争论,倒不如说是辩论双方间的一场意气之争,因为满文文献对清史研究的价值世人皆知,怎么强调都无可非议
(参见杨珍,《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光明日报》,2016年6月1日;乌云毕力格,《清史研究岂能无视满文文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6月19日)。“新清史”家们对满文文献的强调,凸显出汉族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传统清史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中国的清史研究长期以利用汉文文献研究清代“基于中国的帝国”历史为主流,而“新清史”提倡利用满文等非汉文资料,强调研究清代的“内亚帝国”史,对中国的清史研究自然具有批评和讽刺意义。试想大清王朝灭亡才百有余年,可满语早已基本失传,满语和满文文献研究也几成“绝学”,这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也是让整个中华民族都感到十分悲哀的一件事情。今天的中国学者理当具备接受“新清史”家们批评的道德勇气,并对中国清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对自己目前的研究做出及时的调整和改进。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新清史”十分强调满文文献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表明“新清史”家们都是能够熟练利用满文文献从事清史研究的语文学家。“新清史”的学术意义在于,它为清史研究设计了一种新的学术进路,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方法,它的学术追求或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关于清史的宏大叙事,其意义属于意识形态层面。“新清史”学者中间没有任何一位能够像Fletcher先生一样,同时利用满文、蒙文和伊斯兰语文文献来从事清内亚研究,也没有任何一位是真正从事内亚文献研究的传统的语文学家。可以说,迄今为止“新清史”家们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绝对不在于他们发现和利用了哪些前人未曾利用过的新资料,提供了哪些人们以往不知道的有关清史的新知识,或者说,他们通过对满文文献所作的扎实过硬的语文学研究,纠正了哪些传统清史研究中的错误:这些本来就不是”新清史”家们所追求的学术目标。“新清史”积极主张要利用满文史料,这更多是要表明一种学术姿态,但他们自己并不见得一定能够身体力行。笔者翻阅了多部著名的“新清史”著作,查看其书后的征引文献目录,发现它们所利用的满文文献极其有限,其中有好几部甚至根本就没有利用过满文文献,让人怀疑它们的作者是否真的具备利用非汉文文献的能力。看起来,正如多位“新清史”的批评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新清史”的“宏大叙事”多半是建立在他人的二手著作的基础上的。
Johan Elverskog是真正能够利用满文、蒙文文献来研究清代内亚历史的欧美学者,常常站在反对“新清史”的立场上。
总而言之,是否能够利用满文文献根本就不是区分一位清史学者是不是“新清史”家的必要标准,像Nicola Di Cosmo和Johan Elverskog等有数的几位真正能够利用满文、蒙文文献来研究清代内亚历史的欧美学者,不但不是“新清史”家,而且甚至常常站在反对“新清史”的立场上。2012年冬天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召开的一次有关“新清史”的圆桌讨论会上,来自日本的清史和满学研究学者楠木贤道先生曾经打趣说:“如果利用满文文献研究清史可以被称为‘新清史’的话,那么我们日本江户时代的满学研究就是‘新清史’了。”日本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承继的是中亚语文学的传统,潜心从事满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但他们并不是“新清史”家。中国清史研究的主流确实是利用汉文文献来研究“清中国”历史,但在此之外也还有不少专门从事满学和满族历史研究的学者,其中又以锡伯族、满族和蒙古族学者为主,他们的满文能力和满学研究水准远远超越西方的“新清史”学者,他们为整理、翻译满文档案和文献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清史研究的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和学术成就理应得到主流清史学界更多的承认和重视,而他们自然也不是“新清史”家。事实上,中国学者大可不必如此脆弱,对西方“新清史”学家们提出的重视满文文献的主张那么的敏感,就利用满文文献而言,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便利。利用满文文献来推动清史研究具有十分美好的前景,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以积极和乐观的姿态来回应“新清史”的这个批评和挑战。
“新清史”对满文文献之价值的强调还同时引起了一场有关汉文文献之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的争论。传统清史研究的基础是清代的汉文文献,汉文文献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新清史”家,他们在强调满文文献之价值的同时,也并没有否认汉文文献的重要性,他们研究清史时所依赖和利用的史料,最主要的从来都是清代的汉文文献。但是,在海外清史学界和中亚语文学界,有一种说法流传颇广,也颇有影响,即是说与满文、蒙文和藏文文本相比较,与它们相对应的汉文文本中常常会出现不相一致的地方,即有窜改、增删和歪曲的现象出现,言下之意,汉人官员/史家或从来就惯于篡改历史记载。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这种怀疑或即源于后现代史学对任何文本之真实性的根深蒂固的怀疑,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建构出来的东西(Geschichte ist Gegenstand der Konstruktion),也没有任何一个文本不是作者有意图地构建出来的,所以“史料即史学”。从这个角度说,怀疑一个文本的历史真实性是有些道理的。但是,为何人们并不怀疑相应的满文、蒙文和藏文文本的真实性,却只对其中的汉文本有这样深刻的怀疑呢?其实,只要对西藏和蒙古历史书写传统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历史书写完全是按照佛教史观,对他们民族的历史作了十分彻底的改造和重构。传统的西藏和蒙古历史书写,都是一部佛教如何改造西藏和蒙古的历史,所以连西藏、蒙古的祖先都变成了印度释迦王族的后裔,他们的国土又是观音、金刚手菩萨的化土,他们的政教合一的领袖则是菩萨的转世或者转轮王等等。显而易见,在遵循自己信仰的意识形态来建构自己民族的历史叙事这一点上,藏、蒙佛教史家应该说一点也不比汉地史家逊色,甚至可以说他们更在行、更先进、更彻底。
中国蒙古学、满学研究的优秀学者乌云毕力格教授曾经多次强调:“史料在性质上分为‘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两种史料间的差异很大。所谓‘遗留性史料’,就是在其产生之初并无传承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之意图的材料,如考古遗存、档案文件等等。记述性史料则不同,在其诞生之初,便以记载、保留和传承历史为目的。”(语见乌云毕力格上揭文《清史研究岂能无视满文文献?》)可见,像档案文件等“遗留性史料”依然可以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史料”,而“记述性史料”则大概已经可以算作是一种历史“撰述”了。我想对史料做这样的两种分类,既适用于满、蒙、藏文文献,也适用于汉文文献。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时,应该区别对待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但这不是要求我们要严格地将汉文文献资料从满、蒙、藏文文献资料中区别开来,因为绝不是只有满、蒙、藏文资料才是可以当作真正具有史料价值的“遗留性资料”,而汉文文献则一定是经过有意改造过的“记述性史料”。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源出于满清帝国时期的多语种文本数量巨大,其中有双语、三语,甚至四语、五语合体的文本,它们绝大部分都应该算作是“遗留性史料”,并非经过史官整理或者有意识篡改过的文本。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不同语种的文本无疑都是在清宫廷中严格按照官定程序,由兼通多种语文的官员十分准确地翻译、制作出来的,在这过程中很难有人能上下其手,对这些文本中的某个语种的文本做有意的窜改。像清廷公开发布的满、汉双语的诏令、文告,绝大部分都应该出自于满汉兼通的满族官员之手,其间根本没有作为被征服和被统治民族的汉人官员插手的机会。而且,汉人官员中满汉兼通的很少,而满族官员中则比比皆是。今天我们无法确定乾隆皇帝的《喇嘛说》最初是用哪种文字写成的,这四种文字的版本应该不可能都出自乾隆皇帝一人之手,但不管其中的哪个文字版本是乾隆亲撰的,它的其他三种语文的文本的翻译无疑都应该尽可能准确地和乾隆亲撰的那个版本保持一致。如果说满文版是乾隆亲撰,而汉文版是汉人译史翻译的话,试想哪位译史敢于擅改同时精通汉文的乾隆皇帝御笔钦定的文本呢?当然,极有可能这个汉文版也是乾隆皇帝本人御笔钦定的,或者出自他手下哪位精通汉文的满大人之手。总之,因为汉文本中个别语词的字面意义看似与其他文本略有不同,便怀疑汉文本或已遭窜改和歪曲,从而贬低汉文文本的价值,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人们对同一个文本的不同语种版本进行比较,并发现这些版本之间出现字面意义上的差异或不同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马上联想到可能是中间的哪个文本——当然最可能是汉文文本——已经被有意地窜改过了。更可能的情形是,你以为在这两种或多种语文文本中出现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貌似字面意义不同的地方,其实在当时的语文和历史语境下,并没有任何实际的不同,一个今天看来看似不一样的语词或概念,在它们当时各自的语文和历史语境下,很有可能表达的是完全相同的意思。而要弄清它们之间的同与不同,体会同一词汇或概念在各种文本中的细微差别(nuance),正是我们提倡多语种文字文献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乌云毕力格2017年8月12日致笔者信中说:“根据我的经验,满汉文本和蒙汉文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是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个主要是因为内地史学编纂形成了自己的话语表达系统,它对其他非汉文文献中的名词术语、固定表达等很多方面有其套语,比如可汗=皇帝,西北地方=朔漠,蒙古=夷、虏,退回原牧地=遁入巢穴,怀疑=狐疑,等等;此外一些关乎社会制度的名词非常复杂,翻译后会失去原有的意思,比如清代蒙古的所谓奴隶,实际上是一种私属人口,译为奴隶不对,等等。但是把这个问题扩大化,说成两种文本完全是两回事儿,肯定是不对的。”由于汉文之历史叙事和公文书写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和精致的书写传统,其中很多词汇和表达方式很难在蒙、藏、满等文字书写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致使这些多语种的文本表面看起来似乎有一些不同之处,文字上无法一一对应。实际上,在兼通这几种文字的专家看来,这些文字表达方式上的不同只是表面的,其实际内容并无很大差别。而在多语种文本之间出现的这些文字表面的不同之处,正是最值得历史学家、语文学家花力气去做比较研究的内容,把它们简单看作是汉人的故意窜改反而是一件非常不正确和不学术的事情。)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清史研究领域内还很少有人开展对多种语文文献的比较研究,却常常听人或明或暗地批评说:与满、蒙、藏文文本相比较,相应的汉文文本有如此这般的缺陷,不得不说,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它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或者歪曲。
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
欧立德先生曾经指出:“从‘新清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什么只用满文档案的汉文翻译会不得要领。使用翻译过的满文档案并不等于使用满文档案,除非这些翻译出自你自己。这不只是因为翻译可能出错,更是因为没有一种翻译可以传达自己亲身阅读档案所得到的那种感觉。”
(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清朝的国家认同》,387页。)我非常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不能阅读一个文本的原文,而仅仅依赖翻译,就如雾里观花,或隔靴搔痒,是没法真正领会文本所透露的真实信息和微言大意的。但是,对于清代留下的双语或多语的档案文献或诏令、文诰类文本,它们与今人汉译的满文档案文献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之中哪一个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作品,所以不能仅从字面上来判断孰个更准确、更可靠。读者必须仔细比对这些文本,把它们放回到清代当时的历史和语言的语境中,比较、考察不同文本间的细微差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和利用这些双语或多语文献。当然,对那些汉语和满语都不是母语的“新清史”家们来说,广泛和准确地利用双语或多语种的清代档案文献,无疑比中国学者更具挑战性,希望他们能把对利用满文文献的那份重视、谨慎和敏感,也用于他们对清代汉文文献的阅读和利用之中。
萨义德《东方学》
“新清史”于西方的出现,以及围绕“新清史”在中西学界发生的这场激烈争论,可以说是西方东方主义学术传统和它的话语霸权在东方产生巨大影响和强烈反弹的一个经典例子。“新清史”的学术视角和“新清史”家们对其学术研究之主题的选择,显现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之主流学术和社会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兴趣和关注,表达的是西方人自己对现实的关心和他们的学术诉求。于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种族/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所以美国历史学家研究本国或他国历史时,本能地会较多地关注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较少地承认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近一二十年来,种族(race)、性别(gender)和族裔性(ethnicity)是美国学术界最博人眼球的关键词,美国的清史研究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这些学术话语的建构和讨论。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以及在今天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的影响下,“新清史”家们的立场自然会站在相对弱小的民族一边,更乐意替他们发声、代言,只是他们似乎忘了,他们力图要代言的满族于当时可是大清帝国的建立者和统治者,他们并不是弱小的一方,相反汉族则和蒙古、西藏和内亚穆斯林诸民族一样,都是在满清统治之下的被征服了的弱势民族。此外,“新清史”也和西方近几十年来积极倡导的区域史研究有直接的关联,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满清作为一个跨越欧亚的大帝国,其地区历史的意义,甚至超越了它在中国历史书写传统之“王朝更迭”模式中的最后一个朝代之历史的意义。
“新清史”家们继承了西方东方主义学术传统的一贯做法,依然认为“东方”——在这个具体的实例中有时是指整个中国和内亚,有时是专指满族、蒙古、西藏和新疆伊斯兰民族等——是没有能力来表述(represent)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历史、现状、对外关系和身份认同等都必须由“新清史”家们来代替他们进行表述。可是,正如萨义德先生一再强调的那样,所有“表述”(或者“代表”,representation)都有本质上的瑕疵,它们都太紧密地与世俗的东西,如权力、地位、利益连结在一起。而任何将经验(experience)转变成表达(expression)的过程都无法脱离污染。因为它涉及权力、地位和利益,它就已经而且必然受到污染,不管它是否是它们的牺牲品
(Edward W. Said,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4, p. 48)。自然,“新清史”家们大概也难以打破萨义德所立下的这个魔咒。不幸的是,不管“新清史”的表述正确与否,不管它们书写的“新清史”是否与清代的历史相符合,也不管它们是否能为传统的清代历史叙事提供任何新的内容和知识,就因为东方主义,它们就可以凭借西方学术对于东方的长期的强势和主导地位,变成一套强有力的学术话语,形成为针对中国学术的一种难以撼动和打破的话语霸权。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由于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习惯于仰视西方学术的权威,故即使到了眼下这个大国崛起、学术振兴的新时代,我们依然还会顺着惯性,继续仰望着西方学术虚空中不断显现的新星,对他们的学术著作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过高的期待。而当这种热忱的幻想和期待遭受无情的破灭时,我们便很容易因爱生嗔,恼羞成怒,将难抑的悲愤很快转换成猛烈的反击,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学术应该保持的理性和尊严。中国学界对“新清史”投入如此之多的关注,这一定是那些“新清史”家们自己始料未及的,但这或也正是他们最乐于见到的现象。1990年代冒尖的“新清史”之所以到今天才反而成了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中国学者对它投注的热情,以及对它所作的各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批评实在居功至伟。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中国学者的努力才使“新清史”家们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地盘内获得了他们本来并未预计到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当然,我们不得不要感叹,毕竟时代不同了,在仰视西方之星空的同时,我们至少已经无法容忍继续处于被代言的状态,我们迫切需要夺取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需要西方人静下来听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表述。可惜,“话语”这东西并不是任何人可以通过外在的强力,从他人手中任意夺取过来的一个权力,虽然我们已经受过了对西方学术之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想之批判的洗礼,但我们还有自己一时克服不了的短板,即我们还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方式来向西方的学术同行正确地表述我们自己,和他们形成一种理性的、宽容的和有建设意义的对话,从而建构出一套或可由我们积极主导,但别人至少也能听得进去,并愿意与你做进一步对话的“学术话语”。今日之中国学界非常渴望能尽快地与西方进行学术上的国际接轨,但是如何来实现这种接轨,则颇费思量,至今似也无十分成功的先例,我们或可以从这场关于“新清史”的讨论中吸取具有启发意义的经验和教训。
但愿“新清史”将是西方学术的东方主义潮流和话语霸权严重侵袭和冲击中国学术的最后一场疯狂(the last bout of insanity)。当中国足够强大,中国的政治和学术都具备足够的自信时,西方东方主义学术传统的话语霸权就再难如此专横地作用于东方,它必然会在东方学术的觉醒和理性面前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将一定是东西之间平等、理性的学术对话。中国学者眼下或已大可不必继续如此情绪化地去质疑西方“新清史”研究的政治立场和学术动机,也无须再对“新清史”学术之枝节末流和错漏谬误耿耿于怀了。我们倒不如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恢弘的气度,甚至可以拿出我们的“大国风范”,坦然接受别人对中国清史研究的批评和挑战,深刻反思自身之不足和缺陷,然后扬长避短,重新启航。清史研究不管新旧,都必须在充分利用汉文文献的同时,还能尽可能多地发掘和利用满文、蒙文、藏文和伊斯兰民族语文文献,以拓展我们的学术领域和研究视野,对涵盖中原和内亚的清代中国历史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并对清代历史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特别的和重要的意义,做出新的、更有启发意义的诠释,最终发展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崭新的清史研究。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