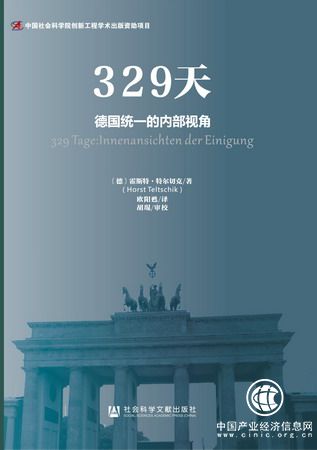如果说冷战是一部在多个不同的舞台上同时上演的戏剧,那么德国必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舞台。我们甚至可以过分地说,在这部“冷战大戏”中最具标志性的开幕和闭幕几乎都在德国这个舞台上演过。1990年10月3日,德国的重新统一注定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为冷战画上了句号。而就在一个多月前,被称为“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去世了,在悼念他时,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必然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再次被人提及。尤其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民族统一”这四个字仍然具有某种强大的魔力,它之于我们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因此似乎有必要从德国人那里吸取一些有关民族统一的历史经验。
(德)特尔切克:《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典藏版),欧阳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来自波恩的声音
仅就中文出版物而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煌煌四卷本的《德国统一史》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有关德国统一历史的最全面、最具学术性的译作。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认真读完这四大本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需要的是更加简单、直观甚至有趣的读物。因此阅读事件亲历者们的回忆录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于是我们可以找到来自美国(布什、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我与东西德统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民主德国(克伦茨:《89年的秋天》,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莫德罗:《我眼中的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等各方当事人们关于德国统一的回忆录。
相比之下,来自于联邦德国亲历者的回忆就显得略有不足。对于想要了解德国统一进程的读者而言,自然需要聆听来自波恩的声音,尤其需要了解当时科尔总理与外交部长根舍在这一伟大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所思所为。然而,这两位重要当事人的回忆是如此的“厚重”(Helmut Kohl, Erinnerungen 1982-1990, München: Droemer Verlag, 2005; Hans-Diertrich Genscher, Erinnerungen, Berlin: Siedler Verlag, 1995.),以至于如今都尚未被译成中文。
科尔和根舍的回忆录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府第二司司长的霍斯特•特尔切克所撰写的这本《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下文简称《329天》)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它为我们观察德国统一提供了一个来自联邦德国的内部视角,它十分完整地记录了从1989年11月9日至1990年10月3日这段时间内,科尔政府为德国的重新统一而努力奋斗的点点滴滴,使我们能够听到来自波恩的声音。
日记还是回忆录?
当我们开始接触这本书时,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无论是在出版社编辑对此书的简介中还是在中译者的后记中,都明确指出说,这是一部特尔切克的工作日志和私人日记。乍一看似乎确实如此,翻开《329天》略作浏览,充斥在书内的日期标题岂不都在告诉读者,这就是一部当事人自1989年11月9日起至1990年10月3日终的日记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沉下心来,再仔细阅读并思考一番后,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一判断值得怀疑。理由如下:
首先,在通读过整部书之后,并没有发现涉及作者私人生活的内容。如果是私人日记的话,读者往往会读到有关当事人的一些生活琐碎之事。可是本书完全是围绕着作者怎样参与处理当时德国统一问题而展开,因此很难说这还是特尔切克的私人日记。
其次,即便将“私人日记”这一措词理解为“个人日记”,而认为本书是一部“日记”的看法仍然是可疑的。一些蛛丝马迹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我决定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的这一天写起;止于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第1页)其中“写起”这一措辞尤为值得注意,具备一般历史文献识别能力的读者们都应该知道,日记应当是当事人在当时的文字记录,所以如果说这本书是特尔切克的工作日记或者个人日记,他似乎更应该在前言中交代自己的长期以来的日记习惯,或者在对本书进行的说明中提及,本书从自己的已有个人日记中摘录编辑出来的,而不应交代自己如何考虑本书从何时“写起”。因此无论如何都可以发现,本书是一部事后写就的作品,而非当时之作。
所以严格说来,本书不是一部私人日记或工作日志,实际上只是一部披着日记外衣的回忆录罢了。克伦茨的《89年的秋天》也属于这一类的回忆录,其第二至五章中同样也是以逐天记录的形式进行叙述,但这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日记与回忆录最大的区别在于时间,一个是当事人在事件发生期间就已形成的文献,一个是当事人在事后对当时所发生事件进行回忆性的叙述。
从史料的价值的角度来看,回忆录比起日记确实要略逊一筹,事后回忆总不如当时的记录。但绝不意味着《329天》这样的书就毫无价值。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作者在撰写其回忆录的时候绝不会仅仅凭借自己的记忆而任意发挥,就如特尔切克自己在前言中所交代的那样:“本书涉及的会晤、会谈、信件交换和声明,都是我在联邦总理府工作时起草加工、分析评价和研究处理的。”(第3页)也就是说,作者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必然会以当时的工作文件作为依据,并以此帮助他进行回忆。如果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作为文献基础,想必这些回忆录也是很难写成的。而回忆录比起日记的优势则在于能够做到紧扣主题、论述符合逻辑、文字表达通顺。
特尔切克何许人也?
特尔切克经历了整个德国重新统一的进程,并且参与了联邦德国政府的决策。因此他对于德国统一的回忆自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首先有必要搞清楚的是,作者当时担任负责人的联邦德国总理府第二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它在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当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本书作者特尔切克
1972年12月21日,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1973年9月18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同时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对于这一事实,两个德国的态度是有很大区别的。联邦德国虽然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国家,承认与它之间的边界,尊重它的领土完整,但仍强调自己同民主德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坚持“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念。与此相反的是,民主德国的领导人们已经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两个德意志民族,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德意志民族,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这种理念上的分歧就直接反映在双方在处理两德关系过程的机构设置之中。
对于民主德国来说,既然两德关系在它眼中应该只是普通的国与国关系,那与联邦德国直接打交道的机构就应该是民主德国的外交部。然而对于联邦德国来说,既然两德关系在它眼中应该只是德意志内部关系,即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之间互不视对方为外国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如果联邦德国把它的外交部当作处理两德关系的机构,则将是对德意志内部关系的破坏,因此在联邦德国政府内,出现一个特殊的部门——德意志内部关系部。它的任务是:为民族统一服务,加强德意志民族凝聚力,促进德国内部两个国家的关系以及承担联邦政府在德国政策方面的责任;在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协调各部门的相关计划。但是此部门开展工作的最大困难在于,民主德国不接受任何和内部关系部的谈判,而只愿意和外交部会谈。所以内部关系部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存在着先天不足,在德国政策方面缺乏政治威望。
真正的核心仍然是总理府,它几乎囊括了德意志内部关系的全部职权。自从1982年科尔就任联邦德国政府总理后,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工作方式,其中科尔作为总理自然是当仁不让的决策中心。另外还有两人值得一提,那便是1984~1989年间任总理府部长后任内政部长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以及本书的作者霍斯特•特尔切克。而他们在科尔入主绍姆宫之前,就已经都是科尔的亲信了。
朔伊布勒与默克尔
在朔伊布勒担任总理府部长之前,联邦德国的总理府部长基本上是由属于公务员系统的国务秘书担任,因此这一职务被视为“最高公务员”。当朔伊布勒以政治家的身份,带着议会选票来就任总理府部长后,这一格局被打破了。朔伊布勒无疑是当时科尔所有顾问当中最重要的一位,在德国政策上,他是首席谈判代表并且掌管着有关德国政策的协调事务。
在总理府下设有若干个司,其中第二司为“外交和德意志内部关系、外部安全司”。特尔切克担任司长,按惯例这个职务一直是由外交部人员担任的。但是科尔上台后打破了这种惯例,而让特尔切克担任这一职务。因为在基民盟还处于在野党时期,特尔切克就已经是科尔的外交政策发言稿的撰写人。但是特尔切克的权力无法遍及整个第二司,在第二司下设有德国政策工作处,它直接受总理府部长领导,从而绕过了第二司的管辖,因此特尔切克本人也很少能够从德国政策工作处那里获取信息,即便该处成员都隶属在他的治下。
这种扭曲的机构设置导致了工作上的重叠,因此朔伊布勒和特尔切克之间有一个分工,朔伊布勒负责德国政策以及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直接谈判,特尔切克则在有关东西方政策的国际事务领域内尽可能发挥作用。而欧洲政策以及德法关系则由科尔亲自负责。这样的一种职务分工,反映了科尔执政时期的一个特征,即在重要部门安排自己的亲信,而并不顾及职衔的高低。从1982年10月开始外交部长如果想要了解德国政策,只能从第二司的副司长那里了解信息,根舍与特尔切克之间仅限于少量的书信往来。于是我们就会发现特尔切克在回忆录中认为根舍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与科尔存在分歧(第225页),对此根舍十分不满,在自己回忆录中进行了严厉回应(Genscher, Erinnerungen, S. 781-782.)。第二司和外交部的矛盾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朔伊布勒借着一次偶然的机会对根舍说:“和一个司长争吵,您不觉得有点孩子气吗?即使他能力再高,那也比不上您啊。”
科尔与特尔切克
这样看似安慰的话语实际上反映的是残酷的现实,即便特尔切克只是区区一个司长,但他也是总理的亲信,他能够不遵循总理办公室的程序和直接接触总理,他能够出席总理和他的亲信们组成的“厨房内阁”,这使他在科尔顾问团队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在1989年底德国统一的进程中,他更是在德国政策领域的操作层面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特尔切克可称得上联邦德国德国政策领域内的第三号人物。这也就是为什么《329天》这部回忆录对于了解德国统一进程非常重要的原因了。
“民族大义”之外的另面
上述所谓的残酷现实其实就是“科尔体制”在德国政策方面的反映,总理在德国政策上是大权独揽的,而且在相应的部门都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担任重要职务。这一相对集中的决策体制为德国最终能在329天内就实现重新统一提供了政策执行力和行政方面的支持。但是要解释1990年上半年的统一进程节奏为何变得越来越快并不容易。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边界的决定是对于国内逃亡潮和民众对于自由出行权以及呼吁政治改革的匆忙回应。当时大家都未能想到,这样一场政治革命最终演变为了民族革命。苏联人强调,开放边界是民主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法国人则担心联邦德国人会为了民族统一而把欧洲一体化进程置于次席,密特朗仍然决定对民主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民主德国基民盟主席德迈齐埃仍认为德国统一并非“此时的话题”。(第21、22、34页)所以在柏林墙开放初期,科尔的态度是小心翼翼、保持克制,避免由于操之过急的决策而发出“错误的信号”(第10页)。
但是边界开放直接导致大量的民主德国公民来到联邦德国,之前“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的口号已经完全被“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的口号所取代。从特尔切克的回忆中可以发现,科尔决定采取积极主动态度来进行应对的时刻,是在11月20日星期一的那个晚上。总理一般会在每周一晚与自己亲信们在总理官邸会共商国是,那晚他们“一直同意,必须将联邦总理极高的国际声望更多地运用到国内政治中,德国问题可以作为桥梁服务于联邦总理的个人形象。”(第37页)这个决定被视为对于德国政策的重新定调,也是之后出台《十点纲领》的前提。
毋庸置疑,科尔积极主动地提出自己有关实现德国统一的构想乃是出于他的“民族大义”,正如他另一本书的标题——“我想要的是德国统一”(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哪些客观现实因素促动他这样去做?看看特尔切克对于1989年11月20日晚间会谈的叙述就可以发现,促动科尔下决心调整政策采取行动的另一大理由是“明年,等待我们的将是马拉松式的选举大战”,正是因为出于这样的考虑,“德国问题可以作为桥梁服务于联邦总理的个人形象。”选票无疑是选举政治下所有政治家们的梦魇,它无可厚非地成为科尔决心积极主动地对待德国统一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联邦政府内部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不单单展示出其身负“民族大义”同心协力、力促统一的一面,其实也表现出了更加复杂的另一面,即国内各政党围绕德国统一所进行的相互角力。《329天》当中曾经提到的另一件事对这一问题同样有所反映。柏林墙开放时,科尔正在波兰进行国事访问,面对紧急事态他决定11月10日下午5点回国,而此时他们接到消息,西柏林市长瓦尔特•蒙佩尔(社民党)呼吁当天下午4点半举行群众集会,并放出风声说联邦总理也将参加。对此科尔感到措手不及,因为他为此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提前回国。对于这件事,特尔切克怀疑这是蒙佩尔故意要让总理出洋相而耍的阴谋诡计(第12页)。
1989年12月22日科尔、莫德罗(左起第一)、蒙佩尔(戴红围巾者)出席勃兰登堡门通道开放仪式
科尔总理自然希望自己能够牢牢掌握有关德国统一进程的主动权。比如特尔切克就提到,科尔曾在基民盟主席团会议上就德国统一这个议题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让社民党从基民盟这里偷走该议题”(第49页)。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尔的所思所忧。根舍也曾指出,特尔切克本人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他(联邦总理)什么都不做,那么这个任务就会有被自民党或社民党接管的危险。”(Genscher, Erinnerungen, S. 670.)使用“危险”这样非常露骨的措辞,自然会引起根舍的不满。这些事例无非说明了,在德国统一的前夜,政治家们并非单凭满腔的民族热情行事,他们的考虑往往要比普通民众复杂得多。
加速统一的客观因素
科尔提出了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但这也只是试图描绘未来统一前景,并不是在为统一制订时间表。(第74页)对此科尔总理是十分谨慎的,反复强调不能“手里拿着日程表去计划”德国统一之路。1989年11月底他本人曾估计,实现统一将需要5~10年的时间,中间还需要经过条约共同体、邦联等过渡形式,最终实现联邦制。当时的同僚们也都认为,即使是到20世纪末才能实现统一,也将是历史的幸事。(第51、49页)所以12月19日在德累斯顿与莫德罗领导的民主德国政府举行谈判时,双方一致同意大家先确定一个小目标:在1990年4月以前建立条约共同体,5月进行首轮自由选举。(第89~90页)
然而形势总是比人强,当时有一个冷笑话是这样讲的:“德国的统一正在成为现实,不过仅仅发生在联邦德国的土地上。”言下之意就是即便民主德国继续维持着它的主权状态,在这片土地上也将不会再有一个德意志人了,民族统一在德国的西部领地内就可以完成了。
据朔伊布勒的说法,1989年来自民主德国的移居者达343,854人,而这一数字呈现跳跃式的增长,没有人清楚地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过境。(第102页)1989年夏天的时候,联邦德国民众对于从民主德国而来的移民还给予热情接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德人、西柏林人也开始抱怨起来——抱怨拥挤的人流,抱怨交通的拥堵,抱怨商店里面挤满了只看不买的东德佬。到了1989~1990年的冬天,对于民主德国人的态度就变得克制很多,不再把他们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难民”。大量的移民对于民主德国而言意味着国家已变成了空架子,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联邦德国而言则意味着国家的住房资源和社会福利体系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而政府对此并未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人对于自己的政权正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昂纳克的接班人克伦茨下台后,权力转移到了政府总理莫德罗手中,看守政府开始与主要的反对派组织、教会和政党联盟领导人进行谈判,以求制定改革的路线图。社会言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许多丑闻被揭露、大量内幕被曝光。原来民主德国国内人均负债总额已经超过波兰,工业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的愤怒和厌恶,对于被揭露出来的国内经济和生态状况的灰心。必然使人产生出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要迅速摆脱当下的困境,最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用最快速度完成统一。
面对汹涌的移民潮,联邦政府担心一旦处理不善,就可能引发社会骚乱。快速统一可能真的是唯一出路,于是科尔也失去了耐心,在与莫德罗政府达成协议的仅仅一个月之后,他就决定不再继续谋求这项协议了。(第107页)他不愿意再继续同莫德罗他们打交道了,认为同它签署任何条约都毫无意义。但是为了防止新一轮难民潮的爆发,在表面上仍还要维持与莫德罗政府进行会谈。(第109页)1990年2月10日,科尔在与戈尔巴乔夫谈到对于统一时间的设想时,他说12月底的时候认为完成统一的时间还是几年,但在此期间民众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表决,如果他对此不作出反应,会非常快地出现骚乱。(第139页)因此,民主德国提前举行选举,效果也十分明显,移民数字开始出现回流,以至于朔伊布勒提出到7月1日为止,停止移民的接收程序和相关的帮助义务。(第180页)
我们原本想要解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德国统一为何如此之快?然而实际上我们或许应该去回答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问题:德国统一为何如此之慢?影响统一进程的与其说是民族热情,不如说是冷静、怀疑以及无动于衷。于是德国统一展现出来的是一幅民主德国民众执鞭催促政治家们向前快跑的画面。
“解锁”戈尔巴乔夫
虽然说主权之事不容他人置喙,但德国统一绝不是德国人自己的事。它直接影响到战后四十五年来的国际政治格局,直接牵涉到美、英、法、苏四大国,北约、华约两大集团以及欧洲共同体之命运。如果要问其中哪一个是关键,无疑就是苏联。科尔认为德国统一能够成功的三个前提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戈尔巴乔夫不能失败。(第74页)如果说“德国统一”这座大门上只有一把门锁的话,它的名字一定是叫戈尔巴乔夫。
当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已经受到了西欧领导人们的广泛欢迎。他对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抛弃,是波兰、匈牙利能够成功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欧洲能够实现持久和平的保障。因此当时类似英国首相撒切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德国统一过快到来,可能将给戈尔巴乔夫带来巨大的问题,他可能因此倒台,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灾难。所以撒切尔认为科尔和根舍应该让其狭隘的国家主义目标服从于欧洲的长期需要。(第115页)密特朗也同样担心德国统一将会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
撒切尔、科尔与密特朗
类似这样的观点自然会引起波恩的不快,但有一点科尔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要努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要苏联不持反对意见,阻挡德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便迎刃而解。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联邦德国倾尽全力帮助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十点纲领》后,科尔就已经预见到,德国要重新统一,可能必须把苏联的债务延期。(第80页)不能危害戈尔巴乔夫,要与苏联进行全面合作,包括安全政策领域的合作。(第110页)1990年1月24日,当在《图片报》读到苏联人绝不反对德国统一的表态后,科尔中午就同意从今后八周之内向苏联供应5.2万吨牛肉罐头、5万吨猪肉、2万吨黄油、1.5万吨奶粉和5000吨奶酪。为了确保友情价格,政府从联邦预算中拿出2.2亿德国马克进行补贴。(第113页)5月中旬,科尔决定为向苏联提供的总额50亿马克的贷款提供担保。(第234页)
有可能正是这样的姿态让戈尔巴乔夫感到,德国的统一并不会让苏联受到什么损失,相反苏联有可能利用这一机会与新德国开展更加全面与紧密的合作。然而不幸的是,苏联的解体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新变化,俄德关系出现了新问题。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苏联继续存在,这类问题就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我与东西德统一》,第138页。)戈尔巴乔夫对于德国统一的基本态度是:这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而正是这样的态度显得有推脱责任之嫌,以至于有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背叛了民主德国。对此,克伦茨的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他“不认为一个外国的当政者会有意成为别国的叛徒。”(克伦茨:《89年的秋天》,第329页。)
还有一项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指责是说他在德国问题上过于软弱。这在《329天》中似乎也可以寻到痕迹。根据特尔切克的叙述,在1990年2月10日与科尔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表示,他知道对科尔而言统一之后德国的中立化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看上去可能会因此抹杀德国人过去为和平所奉献的功绩,他理解德国人的感受,对于德国应该是何种地位要做进一步的思考。为此特尔切克惊呼:对于德国统一的国际地位,“戈尔巴乔夫没有确定最终的解决办法,没有索取代价,甚至没有威胁。这是怎样的会谈!”(第140页)这样看起来戈尔巴乔夫好像对于统一后的德国已经没有任何构想与要求了。这可能确实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戈尔巴乔夫怎么会如此软弱?
但实际上特尔切克的叙述并不完整,不清楚他为什么不提下面这些内容。在这次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十分明确地向科尔指出:“我仍然愿意看到统一后的德国置身于各种军事组织之外,而又拥有确保国防所必须的武装力量。”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当时的印度和中国都是属于这种“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国家,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被贬低,为什么德国人就会因此受到贬低呢?(戈尔巴乔夫:《我与东西德统一》,第82页;Aleksandr Galkin, Anatolij Tschernjajew (Hrsg.), Michail Gorbatschow und die deutsche Frage: Sowjetische Dokumente 1986-1991,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 S. 329.)戈尔巴乔夫在此其实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只是不愿意使用“中立”这个措辞来惹恼科尔罢了。
因此说戈尔巴乔夫过于软弱或一味退让可能并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戈尔巴乔夫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反复强调拒绝统一后的德国是北约成员,但最终结果却都未能如愿。只是在西方国家看来,戈尔巴乔夫的口头呼吁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他们都认为这样的表态是出于苏联国内局势的需要,只是一种策略而已。直到7月16日戈尔巴乔夫才最终明确宣布,不反对统一后的德国继续留在北约。(第319页)
不受信任的德迈齐埃
1990年3月18日,在民主德国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德国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最终它联合社民党与自民党共同组阁,民主德国基民盟主席德迈齐埃就任民主德国最后一任总理。这是民主德国历史上最自由、民主的一届政府,而它的使命就是要结束民主德国的生命。德迈齐埃的任务似乎就是全力加速统一进程,甚至于他被认为是完全听命于科尔的。但从《329天》中反应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简单。
正如之前已经提及的那样,政治家们对于统一的热情远远比不上普通民众,尤其是民主德国的精英们。即便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反对者们也并不认为和平革命的目的就是把民主德国就这样拱手让给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而是应该走“第三条道路”,即追求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此德迈齐埃在边界开放后的第二个周末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主义是人类思想中最美好的形态”,德国的统一并非“此时的话题”,它“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或者孙辈开始进行的”考虑。对此特尔切克认为,“这次访谈加深了我们对德迈齐埃的怀疑。”(第34页)
德迈齐埃赢得选举
为什么要怀疑德迈齐埃?特尔切克没有给出更加具体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不信任感。或许在联邦德国基民盟来看,在长期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民主德国基民盟可能早已变了味,在和平革命之后并还没有完成自我清理的进程。因此特尔切克感叹,基民盟人士在民主德国并没有天然的伙伴,而现在把民主德国基民盟当作伙伴还为时过早。(第77页)
科尔本人也没有多谈对德迈齐埃的看法,只是认为德迈齐埃单独领导民主德国基民盟参与莫德罗领导的“民族责任”政府是一个错误,(第104页)因为当时民主德国的经济已经完全看不到希望,(Kohl, Erinnerungen 1982-1990, S. 1045.)莫德罗已经无力回天,而民主德国基民盟这时还成为政府内的一份子,无疑是在政治上“抹黑”自己。此时科尔早已把目标放在了之后的选举上,2月中他要决定将来基民盟在民主德国的伙伴,但他对民主德国基民盟仍然持怀疑态度。(第113页)
所以对于德迈齐埃在统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即便当他担任最后一任民主德国总理后,他的一些表态在特尔切克看来是明显偏离了联邦政府的路线,尤其是在波兰的边界问题方面。以至于必须同他商谈并纠正之,但又必须小心翼翼,以避免造成一切都是波恩在“遥控”的印象。(第197页)当两德签订了《关于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西德马克都已经进入东德之后,接下来应该是根据《基本法》第23条实现统一,对此德迈齐埃仍在犹豫。(第240页)这到底是他缺乏政治经验和能力的问题,还是他本人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不存在的“两德统一”
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阅读《329天》这样的书,了解有关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自然会把对德国统一的感悟联系到对于两岸关系的思考上。在台湾,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提到过德国统一模式可被两岸借鉴,而提出所谓“亲中爱台”的独派赖清德也同样赞许过德国的统一。因此德国统一的历史经验在当前两岸关系下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向,甚至自相矛盾。因此最重要的应当澄清有关德国统一的历史事实。
首先是要明确,统一前的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内被视为两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它们同时成为了联合国成员国,第三国能够同时与这两个国家建立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两个德国彼此承认对方是主权国家,因此统一之前的两个德国与当前海峡两岸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是要明确,并不存在两个拥有主权的德国重新统一成一个新德国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通常挂在嘴边的“两德统一”或者“东西德统一”的表述其实并不准确,而应该使用“德国重新统一”这样的表达。1990年10月3日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新德国,而只是一个版图扩大了的联邦德国。这是由于德国统一遵循的是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之规定,原民主德国地区以州的形式加入联邦德国,而不是遵循涉及为新德国制定宪法的第146条。因此有人会认为民主德国是被“吞并”的,不过这也并不符合事实,选择结束民主德国的生命正是民主德国的人民自己。
如果说德国统一为当前的两岸关系留下什么宝贵历史经验的话,那应该就是:统一应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而当两岸人民共同具有强烈的统一愿望的时候,任何障碍也都将迎刃而解。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