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老天爷又偷偷下了一夜雪,把整座红安城藏进了雪花中。

“徐传,你喜欢雪吗?”上午在颐和家园扫雪时,同事赵海军一边铲雪一边问我。我停下手中的扫把,凝视了一下他,欲言又止。从我的童年开始,雪,就代表着冬季,更代表着寒冷与寒酸。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农村老屋的房子一排四间,土坯砌成的瓦房,我的床就在东头第一间窗户下。那年春节将至,父亲担心窗口睡觉的我着凉,花了一上午时间,清除陈旧木窗上的杂物,固定上两层尼龙膜。听母亲讲,那些膜是春季孵完秧苗用过的,父亲把有点看相的洗晒后保存下来,留给我封窗抵御寒风雨雪。

那个清晨,一片雪花偷吻了我的脸颊。我惊醒后发现,封闭严实的窗户全开了,尼龙膜被撕成几片长短不一的条形状,在鹅毛大雪的映衬下摇头摆尾;雪花乘机蜂涌而入,在我的床头肆意起舞。“堂屋有火烤,你起床把被子卷一下,等你父亲回家后再弄窗户!”母亲在査看窗户时对我说。入冬以来,每天早上母亲都会在堂屋的地上生一堆火,保证我们兄弟姐妹起床后取暖。母亲生火用的松树根,都是父亲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些没有经过四季存放的树根,需要干柴草当引火。母亲每次生火,要不停地对着柴火吹、不停地扇,在烟雾缭绕中火苗逐渐旺盛起来。 我来到堂屋柴火旁,拔弄着火堆内几个红苕,那是母亲为我们准备的早餐。“苕熟了,可以吃了!"母亲拍了拍红苕上的尘土,去皮后递给我。空腹一晚,在面对焦胡香的红薯,满屋的烟熏味在那一刻荡然无存。

在添加完柴火后,母亲开始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赶做我们期待过年穿的新布鞋。母亲用一块块旧布料,一针一线地缝制着,不厌其烦地调整着鞋底和鞋面的松紧度,直到鞋子的舒适度达到最佳。吃完一个红苕后,我跑到大门处,从门缝中往巷子张望,看看大雪中是否走来父亲的身影。随着柴火越来越旺,堂屋屋顶有几处开始滴水了。因为屋内热量快速上升,火堆正上方的积雪也快速融化,流水顺着瓦沟而下,遇到下方未融化积雪堵塞而倒流。母亲拿了两个木盆,放在滴水较大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自言自语:“滴下来好,雪多不化会压断横梁的…" 不知过了多久,大门被人推开。一身补丁叠补丁的大布单衣,破边的解放单鞋,一手提锄头,一手扶着肩上的大树桩,满脸汗水的父亲站在大雪中。入得家门,母亲递上热毛巾给父亲擦脸,然后用粗浴巾拍打父亲身上的雪。母亲在帮父亲脱衣服时,我发现父亲全身湿透,并冒着热气。我不明白,满身汗水与雪水浇透的父亲,在那样的寒天还有心情说笑:“呵呵,有这个树桩,今冬你们就不会受冻了!”

一直以来,每当看到了雪,我就看到了床头雪花飞舞;看到了老屋瓦缝漏雨;看到了母亲拍打归家父亲身上雪花的画面…… 雪,再见时是安心与踏实,是和睦与温馨,是勇气与奉献。(徐传)
转自:中国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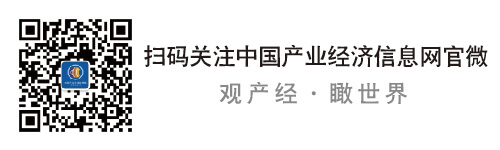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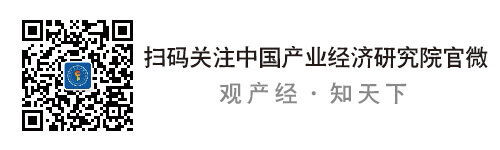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