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城,感觉有些时日没去了。而好好走荡梅城的大坝,更觉得已是比较久远的事了。
一
腊月的清晨,天色是那种略带阴沉的灰白,宛如一块浸过水的幕布,透出丝丝寒意。今天去梅城,心里头那点期待,竟像个少年似的,扑腾着不肯安分。虽已年近花甲,可想起梅城,这颗心总还是温热的——这里安放过我六载求学光阴,十年工作岁月,后来又因着机缘,还主导过严州古城景区的经营。可以说,梅城于我,不是他乡,是故园;不是风景,是眷念。

从七郎庙游船码头起步,这是我想好的路线。沿着自西向东的城墙大坝走,像是要亲手抚摸一遍这古城的脉络。码头还是那个码头,江水拍打石阶的声音,是一种沉厚的、不紧不慢的节奏。可抬眼望去,风景却不同了。桥头立起了雅高酒店,现代的建筑线条简洁利落,窗户玻璃映着天光水色。更远处,跨江的高速公路桥与高铁桥如两条巨龙,并行着伸向天际。钢铁的骨架在铅灰的天空下显出冷峻的力度,带着不容置疑的速度感。我站在这新旧交错的时光里,一时有些恍惚。这是我熟悉的、又有些许陌生的梅城了。
沿大坝向东,不多时便来到定川楼。只见江面上几艘大货船缓缓驶过,拖出长长的水纹。这似曾相识的场景,把一段几乎被岁月尘封的记忆,猛地撬开了口子,汩汩地涌上心头——这里曾是老家麻车运沙船的卸货之地,也是我少年时省船费的“秘密通道”。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十二岁刚到严中,周末返乡的两角五分钱船费,对农村学子而言已是不小的负担。我常与同乡校友结伴,在那时简陋而带着斜坡的大坝上等候搭乘返空的运沙船。遇到心善的船主,会唤我们进船舱避风,舱内弥漫着浓烈的柴油味,却能隔绝江风的刺骨。若是遇上阴脸的船主,我们便主动握起铁铲帮忙扒沙,粗糙的木柄磨得手心发红,汗水浸湿了衣衫。船主看在眼里,紧绷的脸便会渐渐舒展,递过一碗热水,笑意里满是淳朴的暖意。那些在船头吹风的寒日,那些与沙砾为伴的午后,如今想来虽有酸涩,却成了最珍贵的成长印记,也成为我生命河床底处,一块温润的鹅卵石。
二
收起思绪,继续前行。高大的澄清门城楼已然近身。这城门是古城的正门,也是古城的魂魄所在。我进门拾级而上,脚步在古老的木梯上发出空旷的回响。登临城楼,视野豁然开朗,整座梅城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淡彩水墨,尽收眼底。城内变化的确巨大,昔日低矮杂乱的屋舍,大多被修旧如旧的马头墙民居替代,青瓦粉墙,连绵成片,依稀可见当年严州府城的恢弘格局。老街巷弄蜿蜒其间,虽看不太真切,却能想象那里该有酥脆焦香的严州烤饼,有玉带河的水上婚礼表演,有街头魔术与武术快闪,以及众多游客的阵阵掌声。新的生机,就生长在这古老的枝干之上,不显突兀,反倒有种历经沧桑后的从容气度。

从澄清门下来,沿着城墙走,便到了福运楼一带。这里江岸平缓,心也变得格外柔软。就是这一段路,曾盛放了我人生中最平实也最美好的时光。那时我已在这城里工作、成家,也有了儿子。无数个傍晚,夕阳将江水染成金红色,我便会牵着妻的手,看着刚会走路的儿子,摇摇晃晃地在前头奔跑。他穿着小小的开裆裤,偶尔被路边的野花吸引,蹲下来,用胖乎乎的手指去戳,随即又站起来,发出“咯咯”的笑声,那笑声又清又亮,能溅到江里去似的。妻在后面温柔地唤着“慢点,慢点”……。彼时,这一带还是钱江航运公司客轮的码头,每当黄昏,便有悠长的汽笛声“呜——呜——”地响起,穿透暮色,是归家的信号,也是远行的序曲。如今,汽笛声已随旧日的客轮一同隐入历史,唯有江风依旧,拂过面颊时,竟还像是带着当年那孩子笑声的微温,痒痒的,直钻到心里去。
将近青云桥时,我正沉浸在这似水年华的追忆里,忽地,一片意想不到的绚烂,毫无预兆地撞进了眼帘。
是梅花!
就在江畔的泥地上,成片成林,豁然盛放。不是疏影横斜的孤清,而是轰轰烈烈的烂漫。它们就那样不管不顾地开着,粉的似霞,红的像火,一团团、一簇簇,织成一片香雪海。万千梅花在枝头喧闹着,仿佛把积蓄了一整个冬天的力气,都化作了这倾情的绽放。它们开在古老的城墙根下,开在浩荡的江水畔,开在这阴冷的腊月天气里,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一种敢于在肃杀中迸发生命热度的美。
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走近的。就在这梅花深处,倚着江岸,有一座亭子,石碑上刻着“双塔凌云”四个大字,是苏步青先生的墨宝。亭子正好是个观景的绝佳处。我伫立亭中,贪看着眼前的一切。说来也奇,方才还厚重如棉的云层,此刻竟像是被这梅花的精气神所感,缓缓地、优雅地,裂开了一道罅隙。一束天光,金箭一般直射下来,不偏不倚,正正地落在这一片梅林与亭台之上。刹那间,江水亮了,梅花亮了,连那古老的城墙砖石,也泛起了温润的光泽。整个世界,仿佛在一幅黑白水墨画上,突然着了色,活了,醒了。
三
借着天光,极目远眺,江山形胜,一览无余。眼前,正是史称“丁字水”的三江口。新安江自西而来,清碧如玉带;兰江从南注入,水色略深;两江在此交汇,浩荡成富春江,迤逦东去,直奔钱塘。江面开阔,水势汤汤。对岸,南峰塔秀挺如笔,直指苍穹,据说塔顶的那株黄连木,树龄已逾二百载,与古塔一同呼吸着晨昏,堪称奇观。目光北移,巍巍乌龙山如一道巨大的屏风,横亘在天际,山顶积雪未融,在云隙透下的光里,闪着清冷的银辉。而左岸山峦的北峰塔,与南峰塔遥遥相对,拱卫着这千年府城。那塔下,曾是当年方腊起义的点将台所在。想那豪杰当年,在此擂鼓聚将,指点江山,该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这一南一北双塔,锁住这滚滚三江,藏风聚气,成就了梅城千古不变的风水格局。

就在这壮阔的景色里,对着这傲雪的梅花,另一段关于我父亲的记忆,悄然浮上心头。我读初二那年,家里来了两位客人,穿着朴素的中山装,举止谈吐却颇儒雅。他们紧紧握着父亲那双满是老茧与裂口的手,连声说:“郑师傅,谢谢您,真是太感谢您了!”原来,那时政府要修缮北峰塔,需要一批高质量的仿古青砖,每块须重二十四斤,对土质、沙粒比例、窑火温度要求近乎苛刻。家父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土窑匠人,一辈子跟泥巴火窑打交道。他接了这活儿,从选泥,制坯,到火色掌控和封窑时机,他像对待新生儿一样精心。终于,一窑高品质的“二十四斤砖”烧成了,塔得以顺利修缮。父亲后来对我们说,修塔是积德的事,砖要烧得过硬,才对得起天地良心。此刻,我望着云雾缭绕的北峰塔,仿佛能看到父亲当年蹲在窑火前那专注的、被火光映红的脸庞。那塔砖里,有家父的汗水与匠心;那巍峨的塔影里,又何尝没有如家父这般无数普通工匠的沉默坚守?他们或许未曾读过多少书,却用最质朴的方式,参与着历史的书写。这傲雪的梅,这凌云塔,这千年城,不也正是靠着这份拙诚的、坚韧的精神,才穿越风霜,屹立至今么?
带着满心的丰盈与慨叹,我离开江畔梅林,信步走入城东的龙山书院。书院静极了,庭阶寂寂。这里曾是范仲淹任睦州(严州前身)知州时兴学重教之地。站在其塑像前,似乎还能听到千年前的琅琅书声,感受到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气象。而严州这地方,又与那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严子陵有着不解之缘。范公的济世情怀,严子陵的高洁风骨,如同这土地深处奔涌的两股精神泉源,一兼济,一独善,共同滋养了严州大地上醇厚而清刚的人文气质。这气质,化在历代贤官的治理中,化在文人墨客的诗文里,也化在普通百姓如我父亲那般“烧好每一块砖”的劳作中。
步出书院,我忽然深切地感到,这座千年古城,从未老去。它像一株深冬的老梅,根须紧紧抓住历史的岩层,枝干历经风霜雨雪而愈发苍劲,却在每一个属于它的季节,迸发出惊艳的新蕊。那是一种深植于传统、又坦然面向未来的生命力。
此行访“梅”,访的是记忆中的故城,也是风雪中绽放的生机。梅城与梅花,在这冬日里,完成了一次意义深长的互证。它们告诉我,最美的绽放,往往源于最深的积淀。这便是我冬日访梅所得——一份足以温暖整个余冬的慰藉与希望。(作者:郑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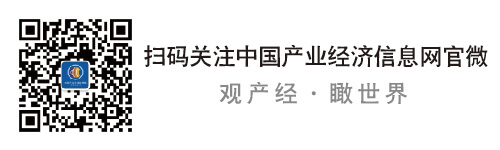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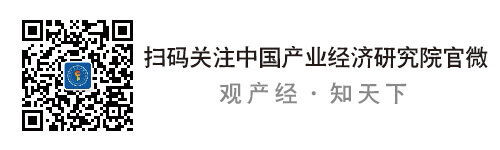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