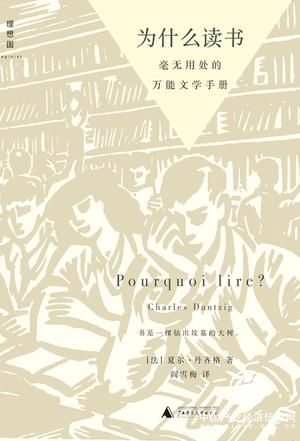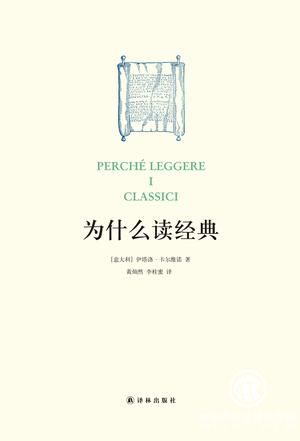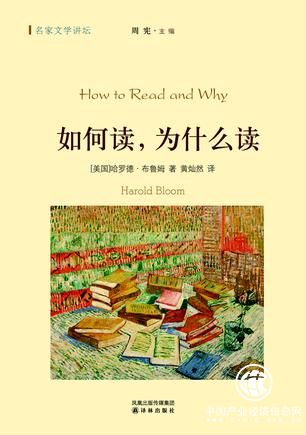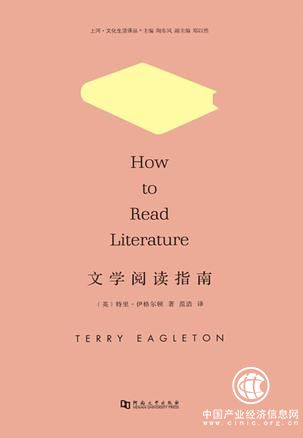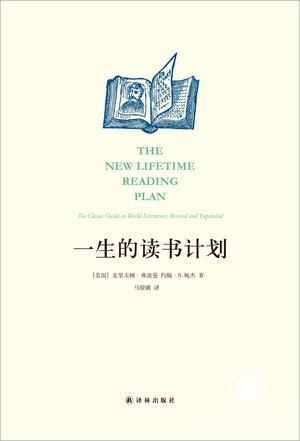哈罗德·布鲁姆也许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如果一个人能活到一百四十岁,他就不用这样笨拙地给我们开列西方经典的书单了。于是,他帮我们读完了那些有趣——但用他的标准来看没什么营养——的“垃圾读品”后,将这些玩意儿pass,然后给我们剩下一堆咬牙切齿才能下咽的精神压缩饼干。
我们能理解布鲁姆的苦心,习惯了文化快餐的人,对所有需要头脑和耐性去揣摩和学习的东西都避之唯恐不及,有多少人愿意努力掌握“古老的语言”去和永恒的经典直接对话呢?
为什么读?
阅读需要理由吗?法国作家夏尔·丹齐格在《为什么读书》中便为读者列出了许许多多理由:“为了爱而读书”、“为了憎恨而读书”、“为了书名而读书”,甚至“为了手淫而读书”、“为了已经读过而读书”、“为了恶习而读书”,这些所谓的“理由”杂糅成了一本书,仿佛在向我们堂而皇之地证明作者就是为了凑本书来骗稿费才读书。其实夏尔·丹齐格是一位阅读的精英主义者,他的口味之刁绝不输哈罗德·布鲁姆,翻来覆去引用的都是福楼拜、普鲁斯特、菲茨杰拉德之类的文学大家。如果你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兴趣看这本书?依我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想和精英阅读的同好们对对暗号。
《为什么读书:毫无用处的万能文学手册》,[法]夏尔·丹齐格著,阎雪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丹齐格自己也知道,热爱阅读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只是同样的意思,卡尔维诺或许表达得更漂亮。他在《为什么读经典》中,为经典下了十四个定义,但言及“为什么读经典”时,“唯一可以列举出来讨他们欢心的理由是,读经典作品总比不读好”。他还煞有介事地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则轶事为证:“当毒药正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支曲调。‘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前可以学习这支曲调。’”这当然等于没有回答。但我们因此倒是感受到卡尔维诺对阅读至死方休的热爱。
《为什么读经典》,[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
如何读?
“你先要找个舒适的姿势:坐着、仰着、蜷着或者躺着;仰卧、侧卧或者俯卧;坐在小沙发上或是躺在长沙发上,坐在摇椅上,或者仰在躺椅上、睡椅上;躺在吊床上,如果你有张吊床的话;或者躺在床上,当然也可躺在被窝里;你还可以头朝下拿大顶,像练瑜伽功……”(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
读者想要习得的,当然不是阅读的姿势而是方法的知识。两位美国学者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编写的这本《如何阅读一本书》,因为书名的“直指人心”而成为阅读方法书的首选。该书把阅读分为四个层次:娱乐消遣(基础阅读)、获取资讯(检视阅读)、加强理解(分析阅读)、增长心智(主题阅读),并着重于第三层次的具体分析,的确极为系统地介绍了阅读的方法,系统到读者准会回忆起中小学时语文老师让我们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的日子,以至于书名完全可以改为《如何解剖一本书》,因此非常适用于理科头脑阅读的社科、理工类书籍。一部文学作品可经不起本书作者这样的“大卸八块”。
《如何阅读一本书》[美]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著,郝明义、朱衣译,商务印书馆
托马斯·福斯特的《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算是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作者总结了二十六个(关于阅读西方文学的)小诀窍,从而使文学的阅读之路变得兴趣盎然。这些小诀窍恰足以成为阅读的佐料而不会像成型的文艺理论一样显出操作的艰深。例如“要是拿不准,可能是出自莎士比亚”,“还是拿不准?那可能是出自圣经”,轻轻拈出了西方文学的源流。“一切皆政治”,“一切皆为性”,精辟总结了受众阅读期待的恶趣味。用这本书编织的渔网去文学之海里做捕捞作业,虽然钓不着大个儿的,但收获也一定不小。
《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美]托马斯·福斯特著,王爱燕译,南海出版公司
相比之下,哈罗德·布鲁姆显现出的是“颐指气使”的大师范儿。《西方正典》“给大师定位”的挥斥方遒,在导读作品《如何读,为什么读》中也处处可见。布鲁姆最擅长的就是精辟地说出各种昏话,以及书单贯口“报菜名儿”。一本小书,就是给自己喜爱的那些诗、小说、戏剧找理由。布鲁姆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鉴赏者,但却不是一个能把道理说清楚的理论家。他给我们总结了如何阅读四大原则:一、清除你头脑里面的虚伪套话;二、不要试图通过你读什么或你如何读来改善你的邻居或街坊;三、一个学者是一根蜡烛,所有人的爱和愿望会点燃它;四、要善于读书,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发明者。但这些“发明”并不比卡尔维诺的“阅读姿势学”高明多少,简明扼要总结起来就是:如何读?照着我的书单读。为什么读?友谊爱情靠不住。妥妥流露出作者既“沙皇”又“宅男”的躁郁性格。
《如何读,为什么读》,[美]哈罗德·布鲁姆著,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
布鲁姆的对手,以理论著称的伊格尔顿,因为忍受不了布鲁姆的牧师气,于是自己也动笔写了本《文学阅读指南》教我们“如何阅读文学”。善于做宣传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当然比唠唠叨叨的老牧师机智幽默,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睥睨与毒舌。此书从开头、人物、叙事、解读、价值五个角度切入文学,施展了作者文本细读的看家本领,虽然偶有过度阐释之处但大体能让人心悦诚服。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哈利·波特》是不值得讨论的,根本不配称为文学,而伊格尔顿则与时俱进地向《哈利·波特》的粉丝拉起了选票。
《文学阅读指南》[英]特里·伊格尔顿著,范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读什么?
伊格尔顿告诉我们可以读《哈利·波特》,布鲁姆认为我们不该读《哈利·波特》而应当去读《哈姆雷特》。两种观点在当今时代的读者支持率很明显,只要去调查一下两本书如今的销售数据即可。然而吊诡的是,阅读《哈利·波特》的读者,接下去读的大约是斯蒂芬·金或《冰与火之歌》,而绝不会是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但阅读莎士比亚的读者,肯定会愿意读一读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剖析。有讨好读者之嫌的行为,并不能留住忠诚的信徒。尽管每一代人开列的经典书单并不相同,但经典阅读的原则就像法律一样不容置疑。什么书是经典,什么不是,也许比如何读、为什么读更需要专业的加持。但这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当年梁启超、胡适都曾为此开撕。法国《读书》杂志的专家就曾出来做过替读者选书的“好事”,编出了一本《理想藏书》,分49个专题2401篇书目。举凡世界各大语种文学,或历险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游记、日记、书信、自传等体裁,或音乐、艺术、历史、哲学、政治、宗教、风俗、美食等专题,都给来了个“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从来没有这样一本书,让中国的读者突然发现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多自己未曾读过的“经典”。不过正如这本书书名所昭示的:第一,所谓“理想”即,它不现实;第二,它只需要“藏”在图书馆里就好了。
《理想藏书》[法]皮埃尔·蓬塞纳主编,余中先、余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们需要的当然不只是书架上吸灰的“藏书”,真诚的读者期待的是一份“一生的读书计划”。然而这个问题同样无法解决,除了每个读者自家的豆瓣条目,没有一份读书计划是能让自己完全满意的。例如克里夫顿·费迪曼和约翰·S.梅杰按照时间顺序笨拙开列的《一生的读书计划》,理所当然会招致口味不同的读者嗤之以鼻。平心而论,费迪曼和梅杰开列的书单并不算坏,但我相信,真没几个人会照着这个方子抓药一样吃下去。所有的必读书目,都可能是另一些人的“不必读书目”。
《一生的读书计划》[美]克里夫顿·费迪曼、约翰·S.梅杰著,马骏娥译,译林出版社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书要教我们如何阅读?张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或可移用于此。昔日张凤翼刻《文选纂注》,有个迂腐的读书人追问,既是文选,为何有诗?张凤翼答,这是昭明太子所辑,干我什么事。那读书人不依不饶:“昭明太子现在哪里?”
张答:“已经死了。”
读书人说:“既然死了,那就不追究了。”
张答:“即便不死,你也没办法追究。”
“为什么?”
“他读的书多。”(卜雨)
转自:澎湃新闻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