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被称为“狂狷之士”的思想者和艺术家,活着的时候,常常被指目为“异端”,为“名教罪人”。
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们其实比孔子之所认同,走得更远,也更具有原创性,而命运的悲苦,思想的无辜,精神的纯良,却莫此为甚。
他们是孤独而骄傲,清醒而自负的。
是他们,让多少有些苍白、有些寂寞的两千年人文历史,显得更加灵动而丰盈;是他们,书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富有个性的篇章。
【孟泽专栏】
漫话中国狂士之郑板桥(下篇)苦痛的傀儡
续接上篇:

影视剧中的郑板桥形象

郑燮像
郑板桥非闭户读书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然无之非读书也。求精求当,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郑板桥《自叙》
苦痛的傀儡
潍县的繁华,板桥在《潍县竹枝词》中有很生动的叙述:“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县原是小苏州”,他还写到斗鸡走狗者的风流,富贵人家的阔绰,贫儿的无助等。美丽的风物、淳厚的民情、世外桃源的理想,自然也时寄笔端。
板桥于乾隆十一年到潍县上任,继续他介于有为与无为之间的治政。
潍县的琐事似乎要比范县多,板桥用富有戏剧性的手段调解了不少纠葛。曾有盐店商人扭一私贩上堂,板桥见私贩衣衫褴褛,料不是歹徒,便对盐商说:
“尔求责扑,吾为尔枷示之如何?”
盐商首肯。板桥就命一衙役用芦席做成一枷,高八尺,宽一丈,上首穿一孔戴在小贩头上,又用纸笔,画竹兰图十余张,贴在芦席上,然后将小贩押送盐店。小贩带“枷”站在盐店门前,铺面全部被芦席遮住,观者如堵,终日不绝。盐商大窘,苦求板桥。板桥笑而释之。
《扬州画舫录》载:有穷书生控某富商赖婚,板桥将书生留在衙中,然后升堂理事。富翁赴诉,板桥从容说:“贵千金若不肯出嫁,请拿一千两改变婚约。”富翁欣然出银千两。板桥又说:“本堂为您择婿,一千银子作嫁资,如何?”富翁谢板桥。板桥便命叫出秀才,公堂成亲,富翁无可奈何。
板桥对穷苦读书人的体谅其实是与他的教化策略相表里的。传说潍县的贫寒书生韩梦周夜半读书,琅琅有声。板桥闻悉,解囊相助,着意栽培,后来韩生果然成了进士,任安徽来安县令,爱民如子。
不仅如此,潍县有钱,板桥主持修文昌阁城隍庙,以宏扬教化。他说:
“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精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
乾隆十一年,潍县发生瘟疫。
第二年又大旱,赤地千里,人相食。板桥拟开仓赈灾,按规定,这不是板桥所能自作主张的。有人委婉地劝他不要仓卒行事,以免获罪于上司,这却大大地伤害了板桥,他说:
“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
便以百姓所写借条批出谷子,活万人。百姓秋后无收成,板桥将借条大多烧毁,象当年他处理家中的契约一样。这极可能误构借公肥私之罪。板桥刻印章一方曰:“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一种道义所激发的情感上的冲动,使他不愿再替自己着想。他限制粮食囤积,平抑粮价,利用县令的身份,劝说富户轮流开设粥厂,煮粥以食老弱贫残,又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亲自规划出修城凿池的工程,由政府集资招远近饥民做工就食。
尽管板桥已尽了心力,潍县依然不乏流离失所的饥民。

郑燮《行书轴》 1756年 122.3X46.4cm 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他很伤心地写下了著名的《逃荒行》《还家行》等诗篇,所述生民苦痛,惨不忍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令人赞不绝口的七绝也作于潍县。
板桥对他的诗歌创作有很多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刻板的要求。他曾在《印跋》中讲到:“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劳人”未必指的全是“劳动人民”,但是,他对诗歌等是否反映了“民间痛痒”却刻刻在心。
按照板桥的正规表述,艺术的原则应该是这样的:“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穷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灵之风猷。”“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归于日用。”“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也”。
基于此,他认为,文章诗歌有大乘法如《史记》杜诗,“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兴亡得失之故”;有小乘法如“六朝”“王孟”,“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
显然,板桥在潍县的诗文是基本按照他的这种主张而写作的,还有前后写的《悍吏》、《私刑恶》、《抚孤行》、《孤儿行》、《故恶》、《田家四时苦乐歌》、《海陵刘烈妇歌》等等。一种对于弱者的悲悯同情,对于善良和道德的珍惜与旌扬之意,浸透了纸背。
在潍县,板桥重订诗词抄,手写印行。在《后刻诗集》中写道:“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他还谦虚地说:“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屡欲烧去,平生吟弄,不忍弃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如何?”
在过于堂皇的标准下,潜藏着艺术取消的倾向。

印鉴“吃饭穿衣”
在给堂弟的信中,他除了告诫家人如何为人爱物,如何长忠厚悱恻之情,驱残忍刻急之性,还教导读书的选择。为了子弟的富贵寿考(他直言不讳这种“私情”,与他论文时常曰生辣曰古奥曰离奇曰淡远的“公道”情形截然不同),他不愿子弟学韩非、商鞅、晁错之文,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学郊寒岛瘦、长吉鬼语。
这简直是近于道学家的口吻了。
潍县任上七年,板桥勤勉而又机敏地应对着鸡零狗碎的大小事宜。其间,还有“乾隆东封书画史”的经历。乾隆东巡,为筹备皇帝登临泰山祭祖、祭天,板桥在泰山玉皇顶住了四十多天,策划布置。后来,他镌印章曰“乾隆东封书画史”,以此自炫自励。
不幸的是,时隔不久,他52岁时饶氏所生的儿子在老家病殁。他曾经常写信托家人教育孩子,一片厚望,以板桥的身世和教养(他显然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要让他反省的是,他是否过分享用了后代的福泽?),以板桥老来得子的亲情,打击可能是巨大的。而在潍县的作为,虽然他自认为时时以古圣贤为楷模,却并不受器重。在给内子堂弟朋友的信中,他屡屡言及他的厌倦和疲惫,“官运有夷有险,运来则加官进爵,运去则身败名裂......惟久羁政海,精力日衰,不仕又无善退之法,自寻烦恼。”“去家十一载,久思解组归田,以延残喘。”“颓唐之象,日渐日衰,作宰十数年,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屡思乞休,遄返故里,与我弟畅叙手足之情,而犹不见谅于当道,殊令人欲哭不得,欲笑不能。”“余已决计告病乞休,若上峰不允,准备一辞不获命,则再辞,再辞不获命,则三辞,务必遂我初服而后已。”
其时,他的身体似不太好,“足部湿气”“通宵无眠”“疝气时发”“左耳失聪”“目光昏蒙”。也许,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他的内心时时跃动着彻底“自由自在”的精灵,特别是当他遇到不顺心的挫折和变故时。
板桥在《青玉案》一词中写道: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绝塞雁行天,东吴鸭嘴船。走词场三十余年。少不如人今老矣,双鬓白,有谁怜?官舍冷无烟,江南薄有田,买青山不用青钱。茅屋数间犹好在,秋水外,夕阳边”。
板桥曾经有卖画扬州的苦心苦旅,有往返于佛道间领略的淡泊况味,这一切,足以让他将天地间以心气相竞的为人,视作无聊游戏的苦痛傀儡,何况琐碎的为官?

郑燮《行书自作唐多令词扇》。释文:绝塞雁行天,东吴鸭嘴船,走词场三十余年。少不如人今老矣,双白鬓,有谁怜官舍冷无烟,江南薄有田,买青山不用青钱。茅屋数间犹好在,秋水外,夕阳边。
三绝诗书画 一官归去来
板桥终于从潍县离任,却是被解职的。
《小豆棚杂记》谓板桥“因邑中有罚某人金事,控发,遂以贪婪禠职”,对照板桥自述“我郑燮之以婪败,今是归装若是其轻且简,诸君子力跼清流,雅操相尚,行见上游器重,指顾莺迁,倘异日去潍之际,其无忘我郑大之淡薄也”,可见他确是“莫须有”的贪婪罪被禠职的。
我们不必把所谓的“贪婪”看得过于认真,也不必为板桥“清白”的人格去笨拙的掩饰,如前所述,他开仓赈灾而将借契焚毁就极可能误构罪责,何况在明清两代,单以俸薪的收入是不大可能在家乡买田地、造屋宇、救贫困如板桥的。
板桥对此也并不觉得突然。
他很钦佩那种能在作官作人方面左右逢源的“解连环妙手”,他也理解到“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生……蛇蜈蚣财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杀之?”板桥其实并不可能“得而杀之”。在一幅送给朋友的长卷中,他画了摇曳有致的兰花,清瘦孤标的竹子,错落的石头,又穿插上荆棘数枝,题曰:“满幅皆君子,其后以荆棘终之,何也?盖君子能容纳小人,无小人,亦不能成君子。故荆中之兰,其花更硕茂矣”。对生命如此豁达的洞察,无疑包括了对于“解职”的始料与不以为意。
板桥终于在61岁时,离开了潍县,头戴岚帽,身穿毡衣,骑毛驴,“囊橐萧然,图书数卷”,还有那把叫“阮咸”的琴。
据说,在他的任内“无留牍,亦无冤民”,百姓感戴,立生祠、祭画像。行时,绅民夹道,不少人持笔墨索书画,板桥画了几竿清瘦的竹子在风中摇曳,题曰: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
然后从容而去。

印鉴“痴绝”
从此江南一梗顽
板桥骑驴而去,扬州秀才李啸村送他一副楹联说: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
“二十年前旧板桥”已然不是“背人独自问真宰”“卖与东风不合时”的落魄板桥了。
扬州是曾经寄寓着板桥的痛苦、相思、落寞、欢乐、疯狂之所在。壮志与辛酸、风流和寂寞,砥砺了他倔强、坚韧而潇洒的品格,把他带入到一种远离“正人君子”的放逐生涯中:
“十年梦破江都,奈梦里繁华费扫除。更红楼夜宴,千条绛蜡;彩船泛春,四座名姝。醉后高歌,狂来痛哭,我辈多情有是夫。”
“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
与落魄困窘同时产生的是无边的愤怒,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叹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也许,就是这种狂怪郁结的生存境况与精神状态,造就了板桥书画的不同凡响。
“六分半书”是板桥融真、隶、草、篆、画于一体而自辟蹊径的“无古无今”的独创,布局如“乱石铺街”,字形怪异、夸张、踉跄不安,又莫名其妙地潇洒清秀。相传,他苦于创新不就,日思夜想,不禁用手在妻子背上横涂竖抹。妻子惊觉说:我有我的体,你有你的体,人各有一体,你尽在我的体上画什么?这平常话象当头棒喝,令板桥禅机顿悟,于是有“六分半书”。
板桥的画以兰竹石写意,苍茫孤独。他说:“予为兰竹,家数小小,亦有苦心,卅年探讨。”“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为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执意地师法造化、集腋古人(曾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青藤,即徐渭),将他顽梗高傲又善良软弱的人格和个性刻画在大自然的平常物件中。然而,它们狭隘又偏执的独特面貌(作为艺术可以不朽),在他当年流寓扬州时,却知音恨少。
重返扬州,“从此江南一梗顽”,板桥心境坦然,不用再有人为他吹嘘捧场。
他在兴化建别业——也就是茅屋三间,但绿围翠绕,容他自在地起居其中,“旧诗书是我有缘物,新见闻是我最乐事。高朋满座,能为破愁城之兵;绿竹横窗,可作入诗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乌兔升沉;借此怡年,亦任燕鸿来往。无心不在远,得意不在多,盆池拳石,居然有万里山川之势;片言只语,宛然见千古人物之心”。
他的生活、他的精神都是自足、朴素而达练的。
他的书画已名闻遐迩,甚至有着“媚俗”的稔熟。盛名之下,不乏无端盲目的趋鹜,“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山中老僧,黄冠炼客,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他为杭州太守吴某画墨竹一幅,吴便“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板桥乐得“过钱塘江、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幽默地享受这“平生快举”。
无时无刻的索画,有时使板桥烦躁。
他不得不贴出价目,以告示巧取豪夺者:“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云云。
更多的时候,板桥愉快地消磨他“酷爱山水,又好色”(自叙)还喜爱吃狗肉的人生晚景。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板桥的朋友,两淮盐运使主持垂虹桥修禊事,文人荟萃,诗酒流连。板桥躬践词场,一和再和。荒城、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他依然保持他那略具病态的爱好与感受,依然保持他那柔弱、敏感的爱心,保持着无愧于生命的坦率与诚信。
他说:“板桥游历山水虽不多,亦不少;读书虽不多,亦不少;结交天下通人名士虽不多,亦不少。初极贫,后亦稍稍富贵,富贵后亦稍稍贫”,“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他清醒地守护纯洁的心性而不致迷失在世俗纷扰中,愁惨的经历与乐天的性情使他具有足以洞悉人生本相的幽默,足以存活自己的精明,足以作逍遥游的智慧。
他其实是表面的颓废派,骨子里的清教徒。
公元1762年,李鱓(复堂)卒,板桥画兰石,并题辞“今年七十,兰竹益进。惜复堂不再,不复有商量画事之人”。
九月,金农去世,板桥在潍县任上时听到这噩耗(其实是病),便为之披麻戴孝,设位而祭。他曾经还为素不识面的袁枚的死(其实未死,误传)而痛哭。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丑而雄、丑而秀”的郑燮板桥,卒于兴化,享年73岁。
其时,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吴敬梓、曹雪芹,用他们“泪多于墨”的小说伤感地“终结”了一个漫长的时代后,刚刚去世。
(郑板桥篇·完)
转自:凤凰国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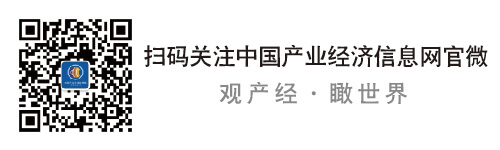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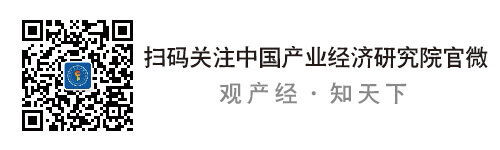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